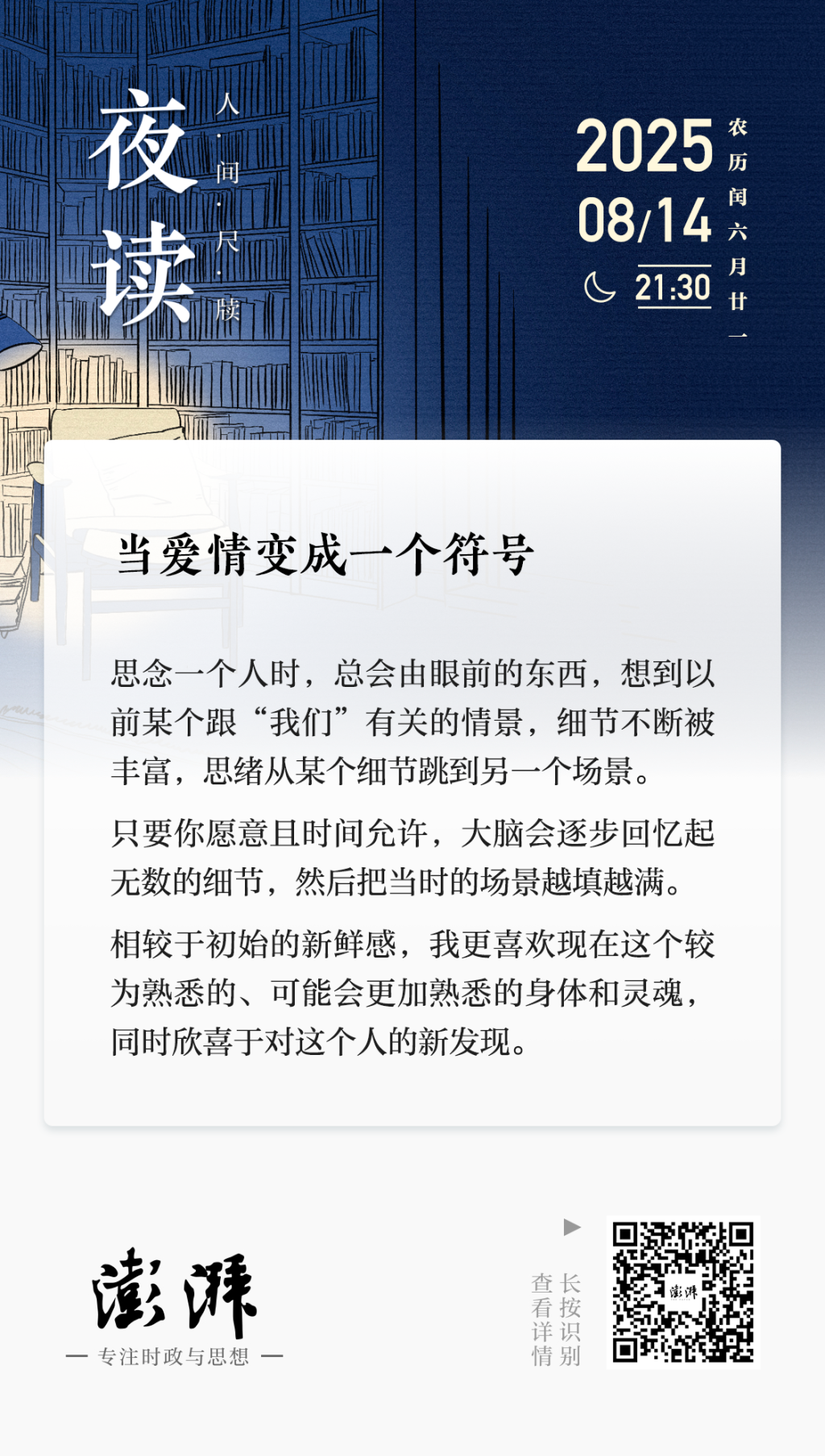在《局外人》中,主人公默尔索入狱之后靠回忆自己的公寓来度过无聊的时间,从粗线条的公寓布局、家具的摆设,到特写镜头一般的沙发套上被香烟烫出的洞。这时加缪写道:在外面活一天,足够支撑在监狱里过一百年。
就像在思念一个人时,总会由眼前的随便什么东西开始,想到以前的某个跟“我们”有关的情景,然后细节不断被丰富,然后思绪又从某个细节跳到另外一个场景。
只要你愿意且时间允许,大脑会逐步回忆起无数的细节,然后把当时的场景片段越填越满,就像不断zoom in的镜头,从大全景一直推到咖啡杯里的绵密泡沫、桌子上一颗香烟灰、眼角的细纹。这些锁链一样的回忆似乎可以是无止境的,直到被现实中的声音打断。
在爱情中,我该怎么准确地描述这种非一镜到底的、由大全景到特写镜头的演变呢?
还是从时间说起吧,像默尔索入狱之后的回忆演变那样。
约会之后的几天里,想起的通常会是我们去了哪里的餐厅或酒吧,那里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景色,我真不应该迟到那么久,以及,见面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先拥抱一下。
再过几天,想起的是我一进餐厅就看到了他,我从门口走到桌前,他放下手机看着我坐下,那天我们吃了什么喝了什么,我们散步的时候路灯昏黄,地面有不少落叶,他还讲到了自己多年前的经历。
再过一段时间,会想起他那天穿了什么衣服,有哪道菜没吃完,他是因为看到某个服务员的样子才讲起那段故事的,他还给我看了一张小时候的照片,那是张幼儿园集体照,他被打扮成了小姑娘的样子……再之后就是更细节的回忆,比如他讲某句话时的语调、他惯用的感叹词等等。
在回忆的时候其实很少会想起当时的自己,或者说,回忆是跟当时的自己无关的,回忆的一切都是有关对面那个人的,他的情绪,他的表情,他的动作。
突然,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我思念的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吗?真实的他和我用感知和回忆拼凑出的他是同一个人吗?我为什么需要这个人?我需要这个人的什么呢?是所谓的情绪价值和情感慰藉吗,是深达灵魂的交流吗,是具体而实在的陪伴吗?
好像都不是,这一切都可以通过别的途径解决,或者说,我在想到以上所有需求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都会出现不同的人——朋友,就可以满足我的这些需求。所以,到底是什么?
如果非要有一个由头的话,大约是某种不常见的、极为亲密的、难以被替代的熟悉感吧。我们所有共同的经历,让我对这个人有了这样独特的熟悉感。相较于初始的新鲜感,我更喜欢现阶段这个较为熟悉的、可能会更加熟悉的身体和灵魂,同时欣喜于对这个人的新发现——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但随着真实的接触越来越少,回忆没有新的情景注入,对这个人的熟悉感只能由那些有限的经历构建,这个人的形象就变得不具体了——不具体并不是样子变得模糊,而是,这个人已经变成了一个“点”——不,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个具象的“·”,而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没有具体形态和具体意义的抽象符号,它既存在又不存在。
它的存在是确定的,因为我的意识里确实有那么一个难以描述的符号。它不存在也恰是因为它的难以描述。
最后,当然,符号消失了,这个人的样子也变得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