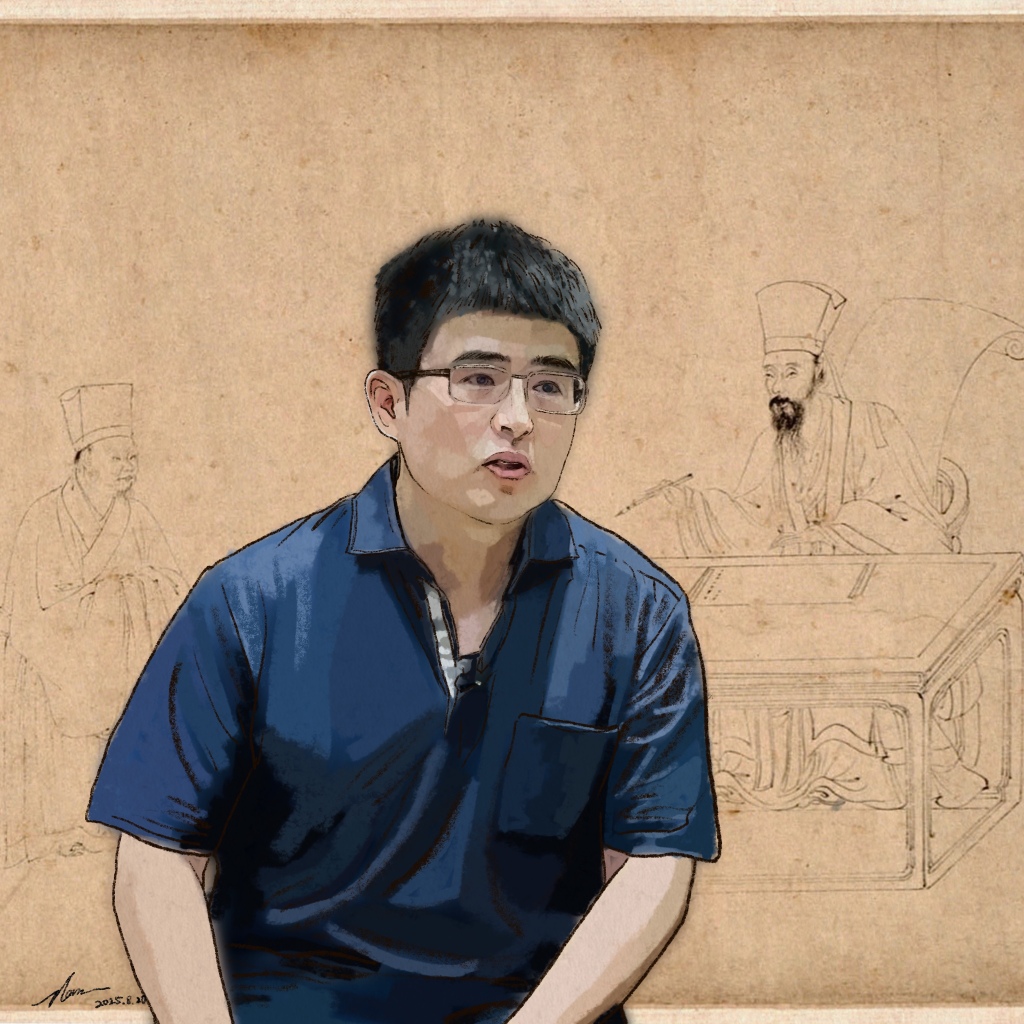
张艺曦(章静绘)
台湾阳明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教授张艺曦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思想史、地方史与家族史,在最近出版的《歧路彷徨: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一书中,他将眼光专注于明中晚期的江西及周边地区的小读书人,展现这些小读书人在晚明各风潮间的徘徊与彷徨,甚至陷入抉择的困境。这些小读书人虽然未能成为主流学术的代表,但他们的活动和选择却深刻影响了明代中晚期的文化与思想格局。在接受《上海书评》的专访时,张艺曦表示:“小读书人的影响力和声音必须逐渐累积起来,而走在最前面的那批人却成了被牺牲的一代,这是令人感到悲哀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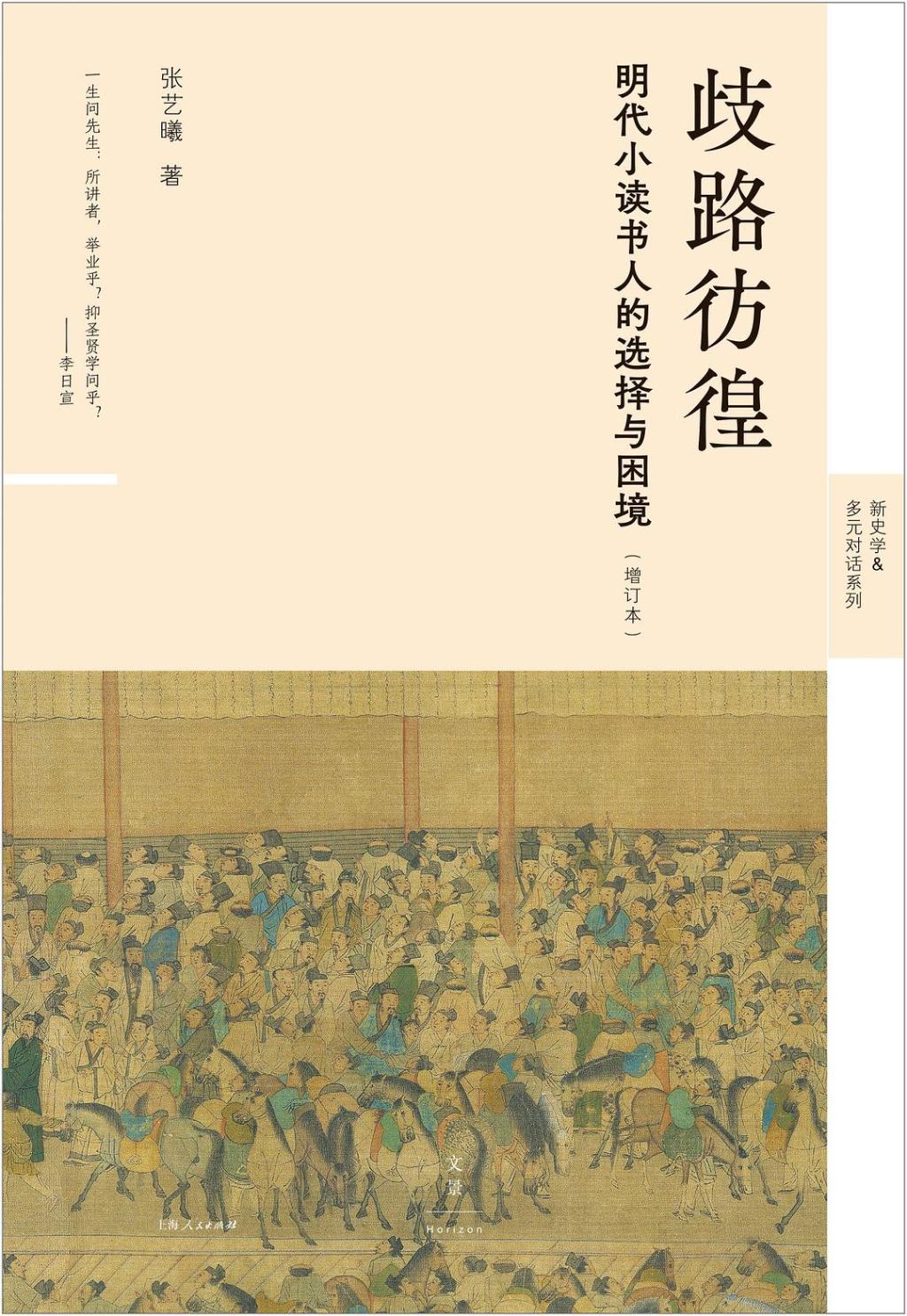
《歧路彷徨: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增订本)》,张艺曦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丨世纪文景,2025年4月版,415页,96.00元
您在导论中对小读书人的定义是“所谓的小读书人,指的是地方上的一般士人,这类士人多半只有中低级的功名,或是没有功名的布衣处士”,不过第七章分析的李鼎,虽然只是举人,但他父亲是广东一带的提学使,他本人与次辅张位是同乡、姻亲,他还曾担任右都御史徐作的幕僚。除了功名欠缺之外,各方面都显示他与我们想象的小读书人相去甚远,是个官二代。您怎么看待李鼎这类人?
张艺曦: *** 上也有人提出类似的疑问。繁体版出版后,便有几位读者在豆瓣读书的评论中指出:李鼎拥有举人功名,而举人在明代已属中高阶层的功名身份,为何将其归类为"小读书人"。这些读者从功名身份、家世背景乃至社会 *** 等角度分析此问题,这种社会分析 *** 本身并无不当。
然而,若从思想文化角度观察,特别是从阳明学群体内部来看,会发现功名身份与讲会角色并无必然关联。即使拥有举人身分,在讲会中也不会特别引人注目。唯一现任官员或掌握政治权力者,才会受到特别尊敬及待遇。进士功名者也会受到特别对待,因此我才将进士排除在“小读书人”范畴之外。
此外,讨论举人或进士的功名身份时,必须考虑区域差异。我所研究的江西地区,科举成就卓著,世家大族林立,举人功名并不被视为特别了不起的成就。但在其他区域,如台湾,便有很不一样的情况:像台湾的竹堑地区,举人功名者已属少见,连生员功名者也很难得。
回到刚才的脉络,实际上还需从思想文化角度考察其角色定位。功名身份对思想文化并非毫无影响,但多为间接作用,这是之一点。第二点涉及李鼎的家世背景,尤其是他如何看待自身家世。纵观李鼎的一生,他始终担任幕僚,并未真正利用家世背景谋求更高职位。诚然,他的家世背景及资源确实使其起点高于一般人,但如果他真要凭借这些优势,理应可以取得更大成就。但实际上,他所从事的仍是一般士人力所能及的事务。此外,他中年流落扬州教书这一经历颇有意思。在明代,扬州往往是失意文人的栖身之地。扬州虽经济发达、人才荟萃,但与南京、苏州相比,更多聚集着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人。这如同学习时尚设计者必去巴黎、纽约或东京,而非京都——并非京都不好,只是在时尚领域处于边缘。同理,扬州在思想文化层面亦属非主流之地,难以跻身顶层圈子。
从李鼎最终落脚扬州来看,他应该在仕途上遭遇阻碍,只是没有相关文献足资佐证。他与谢廷谅、谢廷赞兄弟有往来,而谢氏兄弟曾与汤显祖争夺文化领导权失败后退居扬州,而李鼎与他们在一起,我的之一个直觉是:李鼎应也属于非主流的人物。
李鼎确实处于“小”与“非小”的边界地带,这种边缘性恰恰凸显其特殊性。他拥有举人功名却未加以利用,具有官宦子弟背景却选择做幕僚,最终还到扬州教授八股文。基于这种边界位置,我宁愿将他划入到“小读书人”这一边——他始终游离于官僚体系之外,而未能真正进入主流。
从书名“歧路彷徨”看,您认为明代中晚期的小读书人在各种风潮之间的徘徊,其中,阳明心学和彼时科举科目之间的不协是显而易见的,那些服膺心学的读书人如何接受制艺这一功名利禄之途的?
张艺曦:这也是我在书的序言中特别讨论的问题,即作为学说的阳明学和作为运动的阳明学之间的区别。过去谈论阳明学时,很大程度上受到黄宗羲等人的影响。这跟过去能接触到的古籍资料较有限有关,加上百年来的研究高度重视学术史,因此我们一直将大量精力投入作为学说的阳明学研究上。
所谓作为学说的阳明学,主要是有关大儒的学说思想,以及这些大儒的生平事迹和主要成就。然而,1990年代起陆续出版的古籍丛书——包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丛书》《四库未收书》等——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些资料表明,阳明学不仅是一种学说,更是一场社会及文化运动,而且我们可以更多勾勒出这场运动的发展脉络。
但若将阳明学视为一场运动,大儒就未必是这场运动的主角,反而小读书人才是真正的主角。关于大儒和阳明学说,翻阅《明儒学案》即可了解。但若对阳明心学缺乏浓厚兴趣,这些内容既难以理解,也难以引起深入研读的兴趣。但这就让人好奇:阳明学如何传播到基层民众中呢?关键便在于小读书人的转述和推广,而在传讲过程中,他们对原有学说进行了改造,让基层民众容易理解。
大儒主要是学说及理论的创造者,他们会在书院讲学,吸引小读书人从各地前往书院听讲。此后,小读书人回到所居住的乡里,便会举行乡里讲会,传讲这些学问。但小读书人向基层民众传讲,他们不可能照著大儒所讲的内容来讲,小读书人必须把这些学说及思想予以简化,或截取一面,甚至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扭曲,并结合当地生活实例,用一些身边的事例说明,百姓才能理解其要旨。
简言之,大儒主要在书院讲学,所讲学的对象是小读书人,这些人的数量有限。但小读书人回到乡里举行讲会,这些讲会的数量极多,前来听讲的基层民众更多。所以我才说,从作为运动的阳明学来看,小读书人才是主角。
十六世纪阳明学初兴之际,小读书人对其前景极为乐观。他们对阳明学寄予厚望,甚至有不少人直接放弃科举,专事讲学。我不能说这样的人占大多数,没有那么夸张,但确实不乏其例。可见当时小读书人面对科举持相对乐观态度,认为人生有许多其他出路。
这些出路会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猜测一下。比如说,他们在乡里讲学时,应会有讲学的报酬。再加上他平常可能帮别人做一些事情,比如写状纸,或者在家中开私塾,这样算下来,生活应该不会太差。所以甚至可以放弃科举考试,或者停留在生员阶层,也能安之若素。
然而,约从万历年间开始,整个阳明学迅速衰落,至少在讲学层面如此。这种急剧衰落可能出乎许多研究者的意料之外。一般认为阳明学在万历年间达到鼎盛,但据我研究,其鼎盛之时恰是迅速衰落之始。最明显的标志是:小读书人举行的乡里讲会越来越少了。尽管大儒仍持续讲学,讲到明亡为止,但在万历朝中期以后,小读书人的乡里讲会便几乎都销声匿迹了。从作为运动的阳明学来看,阳明学已中衰了。
与此同时,大量制艺文社(当时把八股文称作制艺)的涌现,于是许许多多的小读书人从乡里讲会离开,转而进入制艺文社中。从某个角度看来,这凸显出小读书人对科举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是在万历朝以后才加剧,在此之前的嘉靖朝,他们的压力相对较小,整体较为乐观。
可把这种变化与当代作类比: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人们若考上大学是很开心的,对未来也充满了希望。但如今情况却已不同,即使考取大学,也对未来充满焦虑。一些大陆学生与我交流时,我能深切感受到他们对未来的不安。某种程度上,这并非学术层面有什么变动或转向,反而是生计等现实问题导致的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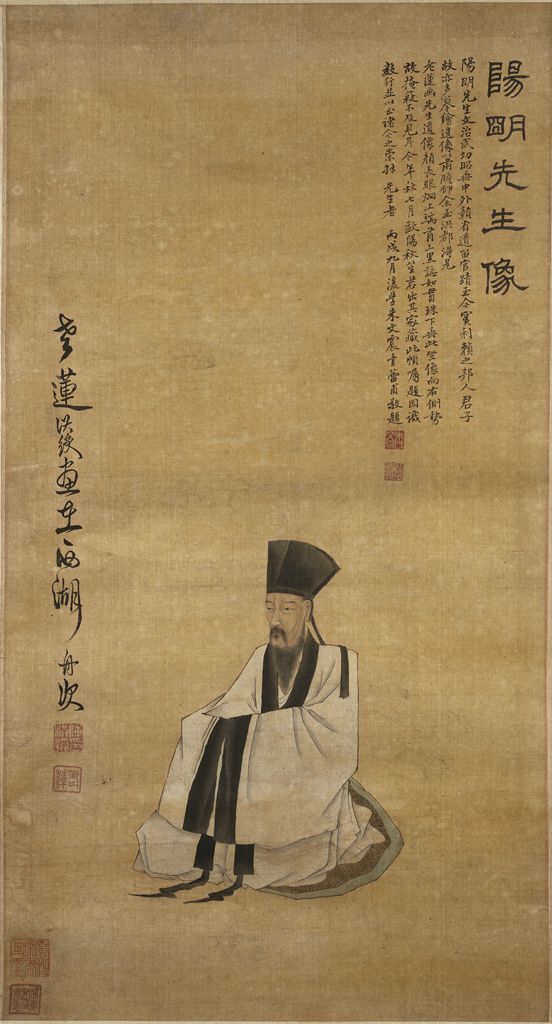
王阳明像
您在书中有大量的篇幅讨论乡间的讲学活动,这些讲学活动既然有强烈的门派色彩,又是如何扩展小读书人的视野的?为什么您认为地方豪强办讲学比大儒办效果更好?
张艺曦:对小读书人而言,开阔视野最直接的方式是游历四方,但囿于生活条件所限,多数人难以实现此愿望。因此,书籍成为他们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明代的出版业发达,书籍流通极广,为知识传播提供很大的便利。此外,阳明学讲会也是重要渠道。在阳明学盛行地区,常可吸引邻近地区的小读书人前往参加讲会。
阳明学初兴之际——约在正德、嘉靖年间,也就是1520年左右——我看到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资料。王阳明为其门人弟子讲学时,往往能够引导听者走出思想困境,让人解开内心的困扰,从某些思想的死胡同中走出来。当时有不少小读书人会形容自己在接触阳明学后有“从地狱脱身、从死亡中复生”的感受,这既说明阳明学说本身具有极强的感召力,但也让我思考,他们在此前的儒学学习中究竟遇到了怎样的难题,才会有如此深刻的心理震撼?
阳明学大约兴起于1520年代,若往前追溯约七十年,就是著名的“土木堡之变”(1449年),这一事件对明朝的政治、社会与思想文化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于是在阳明学兴起以前,理学阵营已曾有新的变革,我个人称之为“新程朱理学的初步变革”。例如成化时期的罗伦、罗钦顺等理学家,便曾有意改革当时的程朱理学,只不过这些改革仍带有较明显的精英色彩,距离一般小读书人的实际需求仍有一定距离。
不过,此时的改革却造成了某种悖论:若儒学完全僵化不变,一些小读书人可能会自行寻求出路;但当罗钦顺等人推动变革后,小读书人却发现理学(或儒学)在改革,但这些改革却与己无关,然后这些人会产生自我的质疑,而陷入更深的困惑与焦虑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阳明学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了出路,帮助其摆脱精神困境。不过,这方面我能引用的资料还有限,目前只能初步判断他们当时的处境。
如前面谈到,明代中后期的讲学方式和书籍传播较前代有显著变化,这极大拓展了小读书人的视野,促使其思想发生根本转变。新的讲学方式突破了传统书院制度的限制,呈现出更加开放和灵活的特点。
不过,当阳明学向地方基层传播时,情况变得复杂起来。阳明学从大儒到小读书人,再到基层民众,会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在文教发达区,小读书人在乡里间的作用较大。但相对的,若在文教不发达的区域,小读书人的乡里讲会则有会遭遇地方豪强的阻挠,倘若小读书人的人数不足,力量薄弱,便很难推广其学说。
以安福西乡为例,这个地方的文教不高,所以当地虽有小读书人,却始终无法举行讲会。等到刘元卿出现,情况才有所改观。他结合家族力量,联合当地小读书人,终于成功说服地方豪强接受阳明学。于是原本难以推进的教化工作,在地方豪强参与后迅速取得成效。安福西乡也成为阳明学传播最快、影响最深的典型案例。
但我猜测,阳明学的传播恐怕也就止步于这个层级。如果还要更下层,恐怕除了泰州学派之外,不太容易找到其他例子。
您在本书中主要讨论的是偏于阳明学的儒生,如果在程朱理学占优势的地区,那些儒生的面向会有什么不同吗?
张艺曦:阳明学不仅在学说上跟程朱理学有别,小读书人的追随,也是阳明学与程朱学的关键差异所在。王阳明本人及他的弟子,以及后续的门人,都吸引了一批小读书人追随,这些小读书人会深入基层讲学。阳明学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便是得力于一大群的小读书人在乡里之间举行讲会,在乡里间向民众传讲学问。
其实在阳明学兴起之前,已有程朱学的流行,但此时的程朱学仍较精英化,对小读书人的吸引力不够,所以跟随的人不多,以致学说的影响力便很受局限。加上没有许多小读书人进入地方基层去讲学传播,程朱学对基层乡里的影响力更小。这应是阳明学在发展初期与同时代的程朱学更大的区别所在。
但两门学问在长期的竞争中,彼此会逐渐发生变化,变得越来越相似。所以你会看到,大概到了万历年间以后,连程朱学也有一群小读书人跟随,而且数量逐渐增多,越来越明显。于是两者之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小。在不断的竞争与调整中,两门学问越来越相似,也越来越接近。
您在书中似乎并未过多描述这些小读书人的生计问题,从您分析的涂伯昌的个案看,他的生活极为艰难,这些人如何维持生计的,他们靠什么坚持下来?我在看涂伯昌的经历时,有些难过,他的妻子陪着他受苦,等到他生活比较安稳的时候,妻子却已经去世了。
张艺曦:生计始终是很切身的问题。无论怀抱何种理想,最终都需直面现实生活的压力。涂伯昌的经历极具代表性:涂氏家族在新城颇有影响力,但涂伯昌却生活困顿。也是涂伯昌的个案,让我有些怀疑,江西的家族势力多大,以及能够带给族人多大帮助。我们或许不能够过度看重家族背景。如果在广东,家族确实势力强大,但如果在江西,家族的影响力或许需打个折扣。
涂伯昌的困境并非个案。这些小读书人虽能找到维持生计的工作,但“活得下去”与“活得好”是不一样的。这颇类似当代台湾地区大学毕业生的处境:就业并非难事,但获得理想职位却殊为不易。从现存史料判断,嘉靖朝的小读书人生活状况似乎相对较好,但万历朝以后,尽管这是被认为明代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但吊诡的是,恰在此时,小读书人对生计的焦虑却日益加剧。他们虽能“活得下去”,但已不是“活得好”的状态。
我想举我自身的例子说明:我在大学时期,学费及生活费都是我自己做家教赚来的。当时的学费没有很高,所以家教的收入还足以应付这些费用。但今日的学生,学费是我当时的三倍,他们即使从事同样的家教工作,也不容易支付全部的费用。这显示同样的劳动,在不同时代却会有不同的结果。尽管我们没有足够资料可以确定当时小读书人的生活状况,但我推测,明代小读书人可能面临类似困境:付出同等努力,却难以获得相应回报,由此功名变得越来越必要,也因此让小读书人对功名越来越焦虑。
另一方面,阳明学也对小读书人形成某种负担,就像涂伯昌一样,他为了学习阳明学,必须出外寻师访友,长达两年之久,最后无功而返,让他悲从中来,在舟中放声大哭。此时的阳明学已不像初期一样,让人从地狱中脱身,反而更像是一门功课。
但偏偏麻烦的是,小读书人不能不作这门功课,因为他们已无法回到阳明学出现之前的状态。阳明学开拓了他们的视野,带来了新的思想资源,使其难以再回到过去的思想蒙昧时期。这种情况颇似智慧开启后的困境:一旦获得新知,便无法回到无知的状态。然而,这种觉醒有时反而成为负担——新的认知让他们无法满足于现状,反而带来更大的精神压力。这或许就是“知识的诅咒”:知道得越多,痛苦可能越深。
在您看来,晚明制艺风气的兴起、阳明学的衰落,主要的原因是什么?除了乡村经济的凋敝,是否还有政治时局的动荡或思潮变迁的原因?
张艺曦:我认为大致上会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经济是基础,对此我们基本上不用怀疑。一定是在生活及经济压力下的结果,使其转向制艺写作,及对功名的追求。另一方面,则是我今年底即将出版的《与世浮沉:明代江西思潮、社集与小人物的追寻》要谈的论点,也就是阳明学在万历朝中衰的同时,有一股新的风潮起来,我称之为制艺风潮。制艺就是八股文。这是由小读书人的群体动向所逼出的新风潮,这股风潮引领小读书人把眼光的焦点从阳明学转向制艺写作,制艺成为知识的轴心,而阳明学只是作为思想资源,而被制艺写作所用。
这股风潮是由小读书人的群体动向所造成的,而不是由大儒主导的,这非常特殊。其实,大儒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能够主导全部一切。大儒会受到听众的影响,而当小读书人越来越关注功名时,便会逐渐影响大儒的讲学内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比如邹德泳,他是在《明儒学案》中有名的人物。他很早就考取进士,晚年大约七十二岁时,却在书院跟小读书人谈八股文,还把自己写的八股文拿给他们看。我们知道,明代的大儒很重视自己晚年的评价,但邹德泳却是在晚年做这件事。这显示:小读书人对八股文的关注,使得本应该讲授阳明学及心性义理学说的大儒,不得不与小读书人讨论八股文。
又比如我们在高校教书,当我给学生上课时,学生的反馈会促使我调整讲课内容。而一门课程能否吸引学生也很重要,如果学生对某门课程没有兴趣的话,这门课可能就开不成。相对的,学生有兴趣的知识,校方就会督促系所开设相关课程。
这种小读书人群体的诉求和走向,我称之为群体动向。一开始的时候,只有零星的一些小读书人有这样的走向,但慢慢地这类倾向越来越普遍。当越来越多的小读书人关注制艺写作时,大儒为了吸引小读书人,就不得不表态说:我也是进士,我也会写八股文,我们可以一起讨论。明末的制艺风潮,实际上就是由一代又一代小读书人逐渐累积形成的结果。
您在书中讨论了净明道和龙沙谶对小读书人的影响,晚明儒生偏好净明道可以理解(即使净明道也偏于民间秘密宗教),但他们——不管是学程朱还是学阳明——都经过了儒家理性主义的洗礼,为什么对龙沙谶这类荒诞的预言也如此痴迷?痴迷谶言,是否意味着他们对未来的绝望?
张艺曦:理学确实比较强调理性,我的老师王汎森先生便谈到,宋明理学的特色之一是“去魅化”,不过,这里的“去魅化”不能完全用现代社会的视角去理解。明清时期,人们对“迷信”与“非迷信”的界限,与我们今天的标准并不完全相同。当时的人并不会把地理、风水视为迷信,但在当代社会则往往会被归入迷信范畴。我们今天之所以把界限划得很清楚,是因为经历了二十世纪以来科学主义的影响,对“迷信”的定义也比明清时期严格得多。对于李鼎个人而言,龙沙谶本身并不算迷信,他认为这个谶言跟他所习的儒学不仅不冲突,而且是可以相调和的。
值得一提的是,龙沙谶其实是带有末世色彩的预言,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言说,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不安或经济危机造成的。相反的,李鼎所处的万历朝,龙沙谶预言流行的江南及江西一带,社会及经济状况都蛮好的,甚至是很有享乐的气氛的。可能正是这个缘故,以至于龙沙谶流行到后来,蛟龙作乱这个环节甚至变得不重要而被忽略了,大家关注的反而是“谁在仙籍里”。而且由于在此世的生活太舒服了,当有人知道自己的名字在仙籍后,还进一步问:“飞升之后,我的财富能不能一起带走?”他们想象的不是国家或世界即将毁灭,而是升天以后还能继续享受生活。
当研究龙沙谶时,我常常会联想到1990年代的台湾地区。那时经济颇繁荣,宗教活动异常活跃。打开电视,几乎每个频道都在讨论宗教话题。但当时大家很少有末世的感觉,人们并不是因为绝望才信仰宗教,反而是在物质生活优渥的情况下,仍然渴望精神层面的满足。
所以我认为晚明的情况其实有点复杂。一方面,经济形势依然良好;但另一方面,社会确实存在某种心理焦虑,人心浮动不安。这是一种多层次、复杂且交织的心理状态。但这不一定是“末世”的心理。我们若是观察当时的一些术数之学,明亡于1644年,但即使到了1620年代,许多明朝人依然坚信国家即将迎来盛世,而且这场盛世将会持续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黄宗羲所相信的“十二运”的预言,就认为明朝即将进入极为辉煌的时期。江西的很多人,包括涂伯昌在内,也觉得明朝快要走大运了。
还有一个例证:1620年代有魏忠贤及阉党当政,按理说政治已经极度腐败,但许多人却把这看作是“黎明前的黑暗”,相信崇祯即位、魏忠贤倒台以后,局势就好转了。“末世感”并没有成为主流声音。尽管任何时代都会有人觉得“这个时代很糟糕”,但在李鼎所处的那个时期,这种看法并未成为社会的主流声音。
小读书人某种程度上只是明中晚期思想文化风潮的尾端,他们受时局变迁和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很大,而对主流的影响相对较小。当然,您也提到他们对阳明学的质疑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不管怎么说,整个明代的发展起伏,小读书人能起到的作用还是有限的。从某种意义上,有点我们像现在说的小镇做题家那样,会有一种无力感。面对国家、民族或整个思想的大变局,这些小读书人虽然可以努力抗争或回应,但他们毕竟还是处于大变局的尾端,这难道就是他们的宿命吗?
张艺曦:前面提到明末的制艺风潮时,我尝试从乐观的角度去探讨它所带来的积极意义。然而,其中也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由于小读书人要积累出足以影响时代的力量和动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于是往往会有一代人成为牺牲品。
以我个人的经历为例:我毕业求职时很幸运地找到教职,但在我之后好几届的学弟、学妹却在求职时屡屡碰壁。直到最近,台湾地区当局才开始正视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个过程已经延宕了十年之久,其间有整整一代的博士生被牺牲。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 *** 或许永远不会意识到这个结构性的问题。但等到政策真正改变时,受益的其实是下一代人。这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这几乎是小读书人群体的宿命——他们的影响力和声音需要长期积累,而走在最前面的一批人,却往往会成为被牺牲的一代。这实在很令人唏嘘。
谈到当今的小镇做题家,其实和明代的小读书人颇为相似。当时的小读书人在准备八股文时,会读大量的选本,这些选本收录了先前几届科举考试中考取举人或进士的人的优秀文章。但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获得最新选本的速度不一。江南地区新印的选本,可能在两三年后才会流传到某些地区。又或者必须等江南人士外出做官或旅行时,发现某地没有这些选本,方才引进。这导致各地科举考试的资源分配并不均等。文教发达区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考试时自然更有优势,相形之下,偏远地区是居于劣势的。
不过,明代的科举考试与现代的升学考试还是有一些不同。以我熟悉的台湾地区的高考为例,其实很像是一场装备竞赛。家庭能够为你提供多少资源、能否补习、买多少参考书,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但八股文的写作稍稍有点不同,它其实有点接近诗歌创作,虽然可以训练,但仍需某种天赋,这种天赋往往难以世代相传。即便基因好的人家所生的孩子不会太笨,但他们未必传承了八股文的天赋,尽管家世资源可以提供更多训练机会,但无法完全取代个人才情。相对的,一些贫穷人家的孩子,仍有可能依靠天赋而考取功名。所以在明清时代,不少偏远地区的人也能考取进士,这是个人才能的展现,而不会被“装备竞赛”完全压制。反观当下的台湾,无论你多有天赋,如果没有优越的“装备”,在高考中也很难脱颖而出。这也让我反思:人类的文明究竟是在进步,还是在某些方面悄然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