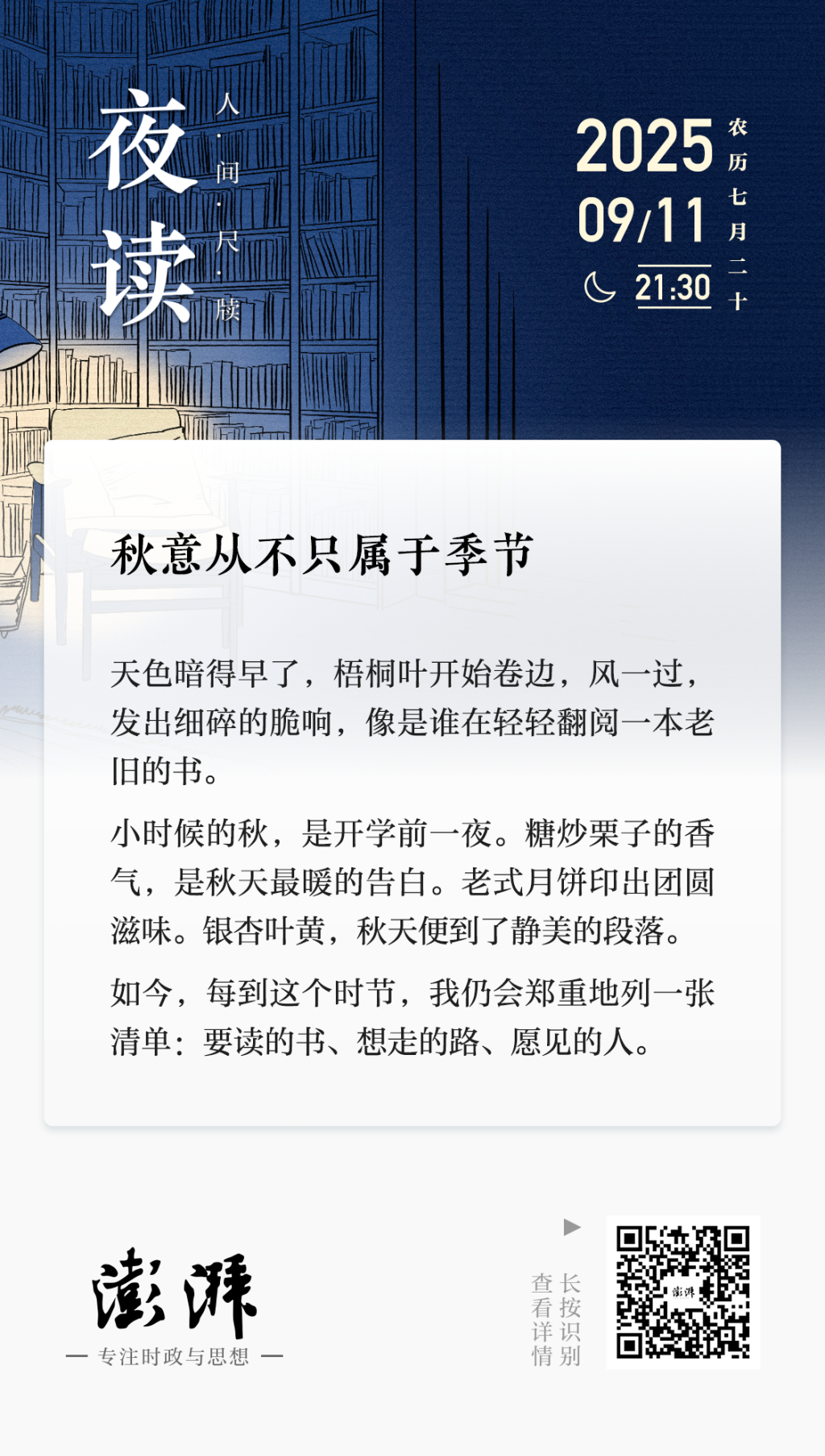不是陡然惊觉的那种,而是无声浸润的凉,像墨滴入水,缓缓漾开一片澄澈的黄昏。天色暗得早了,傍晚五点钟,西边的云已染成橘红色,如同被时光炖得软烂的柿子,透着一股温柔的暮气。窗外的梧桐叶开始卷边,风一过,就发出细碎的脆响,像是谁在耳边轻轻翻阅一本老旧的书。
日子忽然就慢了,人心也忽然静了。思绪如叶,一片、两片,安静地落,铺满来路与归途。这个季节,总让人无端想起一些遥远的事,想起某个午后阳光斜照进教室的斑驳,想起之一次学会骑自行车那个微凉的傍晚,车轮碾过落叶时发出的咔嚓声,清脆得像是一整个童年。
小时候的秋,是开学前一夜。新书包、铁铅笔盒,透着墨香的课本,还有那种翻书时指尖微凉的触感——一切都像未启的信封,藏着一个孩子对世界最初的想象。母亲总会提前把我的校服熨得平整,放在床头。我偷偷摸一摸平整的衣领,闻一闻那股阳光晒过又经熨斗加热的特殊气味。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望着窗外天空中闪烁的星星,听着蟋蟀最后的鸣叫,数着心里那份雀跃与忐忑。
如今,每到这个时节,我仍会郑重地列一张清单:要读的书、想走的路、愿见的人。像是在时序更迭的缝隙里,悄悄为自己埋下一些期待的种子。我还会去买一个新的笔记本,封面是牛皮纸的,内页空白,仿佛可以写下整个秋天的诗。
街角糖炒栗子的香气,是秋天最暖的告白。小摊支在梧桐树下,一盏昏黄的灯,一口黝黑的大铁锅,老师傅戴着手套,挥动铁铲,栗子在黑砂中翻滚,裂开金黄色的笑脸。买一包捧在手里,热乎乎的,像揣着个小火炉。有时候也会购买生板栗,一家人围坐在煤炉边,栗子在铁锅里噼啪地响。我们笨拙地剥,急急地吃,嘴角沾着褐色的脆皮。父亲总会挑出最饱满的一颗,剥好了放在我碗里。母亲总是笑着说:“慢点,烫呀。”
如今那样的夜晚不再有,可那香气一如往昔,只一缕,就推开记忆重重的门。现在的我,也会偶尔买一包炒板栗带回家,倒在白瓷盘里,一颗一颗慢慢地剥,仿佛剥开的是时光的壳,尝到的是从前的暖。
中秋是一年中最浪漫的节日之一。从前的月饼用油纸包着,红绳一扎,甜得朴实、真切。母亲会自己熬豆沙,炒芝麻,包进酥皮里,用红色的食用色素在饼盖上点一个圆点,像是月亮的印记。烤月饼的时候,整个家都是暖香。如今礼盒琳琅,我却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于是总固执地寻找老式月饼,豆沙、五仁、酥皮……一口下去,仿佛咬碎了时光,溢出从前家的温度。今年我在老街巷尾找到一家坚持古法 *** 的小作坊,老师傅说,他用的模子还是他爷爷那辈传下来的,花纹已经有些模糊,却印出了最真实的团圆滋味。
银杏叶黄时,秋天便到了最静美的段落。我喜欢去公园,挑一个长椅坐下,看书,或者只是看叶子一片一片地落。阳光透过枝叶缝隙洒下,光斑在书页上跳跃,像是文字里逃出来的精灵。偶尔拾起一枚夹进书页,像是收藏了秋天最轻的一声叹息。风来的时候,整棵树都在唱歌。我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却仿佛与自然完成了一场深刻的对话。公园深处的荷塘只剩残枝,斜斜地插在水里,有一种颓败的美。偶尔有老人提着鸟笼走过,笼里的画眉叫声清亮,穿透午后的宁静。
秋意从不只属于季节。它属于每一个愿意低头拾取回忆、抬头继续前行的人。属于那些在晨光中扫街的人,在夜市里摆摊的人,在书桌前疾书的人,在厨房里煲汤的人。属于所有认真生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