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陀氏五经”之一,是作家“土壤派”思想观点最直接的体现。在俄国19世纪60—70年代各思想阵营激烈纷争的背景之上,作家将社会批判、精神探索、爱情悲剧等多条线索糅合起来,创作出这部结构精巧、思想深邃的杰作。
2025年6月25日,译林出版社邀请首都师范大学燕京讲席教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刘文飞,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张猛,以及《群魔》译者、厦门大学助理教授李春雨三位学者,在线上一起畅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及《群魔》的永恒魅力与当代价值。刘文飞归纳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十种读法,总结了阅读《群魔》时要注意的“远近”“平衡”问题;张猛探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罗斯现当代文学、电影创作的深远影响,为我们呈现了作为“先锋派美学先声”的陀氏艺术;李春雨则从翻译策略的角度分析语言细节,让我们看到作家是如何通过锤炼字句,实现对人物心理的精准刻画、传递出丰富的审美意蕴的。
以下是这次对谈的回顾文稿。

线上对谈截图
刘文飞: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更多打开方式
米尔斯基在《俄国文学史》中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四部“思想小说”(《罪与罚》《 *** 》《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时,提出了陀氏的四种读法。之一种,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每部小说都看作社会生活的如实记录。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我这一代学者最熟悉的读法,即把文学作品看作对现实的反映。我们讨论它跟时代的关系,跟社会、生活的关系,尤其强调作家本人在作品中对现实的态度。就是基于这种读法,《群魔》在苏联和俄罗斯的接受史上起伏更大。在激进主义占上风的时代,《群魔》一定会受到贬低;而在一个保守的时代,《群魔》就会受到推崇。这就是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现实主义读法”。第二种,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看成宗教文本,把陀氏看成先知、布道者。这种读法看重的是他作品中的精神内涵,这也正是他如今在全世界特别走红的原因。无论读者是否有基督教信仰,都必然要从宗教角度来看待陀氏的作品。第三种,把陀氏的作品看成他的自画像、他的第二自我。无论是非虚构作品中的他,还是他在虚构作品中塑造的主人公,我们都会把他们当成作家本人,都会在这些人身上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读大作家的作品,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觉得,作家本人就站在作品背后。第四种读法,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当成“情节小说”,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悬疑小说、惊悚小说。在同时代的作家中,陀氏是最会讲故事的。托尔斯泰当然也是讲故事的高手,但托尔斯泰讲的是历史故事、爱情故事,而陀氏讲的是当代故事、离奇故事。一个是贵族口味,另一个是平民口味,重口味。当然,米尔斯基说到这一点时,或多或少带了一种淡淡的嘲讽。他的意思是,陀氏比同时代的小说家畅销,是因为他的作品“有料”。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两人的写作动机是不同的,托尔斯泰坐在庄园里,闲来无事,就想教育人类;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要还债的,如果写得不好看,书就卖不出去。以上就是米尔斯基所归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四种读法,对我们的启发还是很大的。
后来在一次讲座中,我又补充了四种新的读法。之一种是比较的读法。白银时代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写过专著《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称托尔斯泰为“肉体的作家”“生活的作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灵魂的作家”“精神的作家”,从此对这两位作家的对比就流行起来了。后来大家也开始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果戈理、屠格涅夫、加缪等作家对比。仿佛陀氏可以拿来跟世界上任何一位大作家作对比。这样的比较还在持续和扩大。现在还可以看到陀氏被拿来与中国作家,如鲁迅、郁达夫等进行对比。第二种读法,来自我们俄罗斯文学专业的人都特别熟悉的巴赫金的贡献。他的“复调”“对话”“狂欢”等理论,都是在解读陀氏作品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也为我们阅读陀氏提供了巨大的空间。第三种是现代派的读法:也正是从巴赫金活动的那个时期开始,大家开始把陀氏看成现代派的鼻祖。对潜意识的描写,以及意识流、结构倒置、作者面具等现代文学中的手法他都用过。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存在主义了。加缪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自己的思想先驱,所以大家都认为陀氏是世界文学中最早的存在主义作家。第四种读法是把陀氏的作品看成“思想小说”。这个定义是苏联文艺学家恩格尔哈特提出的,他把陀氏的作品看作一个独特的类型。陀氏的主人公不是人,而是思想,他的作品就是他本人思想的传声筒,他的作品就是思想史著作。
后来我又加了两种读法,我认为是我们在以前的阅读中所忽视的。之一是从写法、从形式的角度去读他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太强大了,反倒让我们忽略了他的形式。恩格尔哈特反复强调他的作品是一种体裁,一种类型,其实就是把内容当作形式来读的。第二是读译本、读翻译。最新的译本在传达原作的现代性这方面无疑是更好的。
以上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十种读法,而具体到《群魔》,又有一些新的角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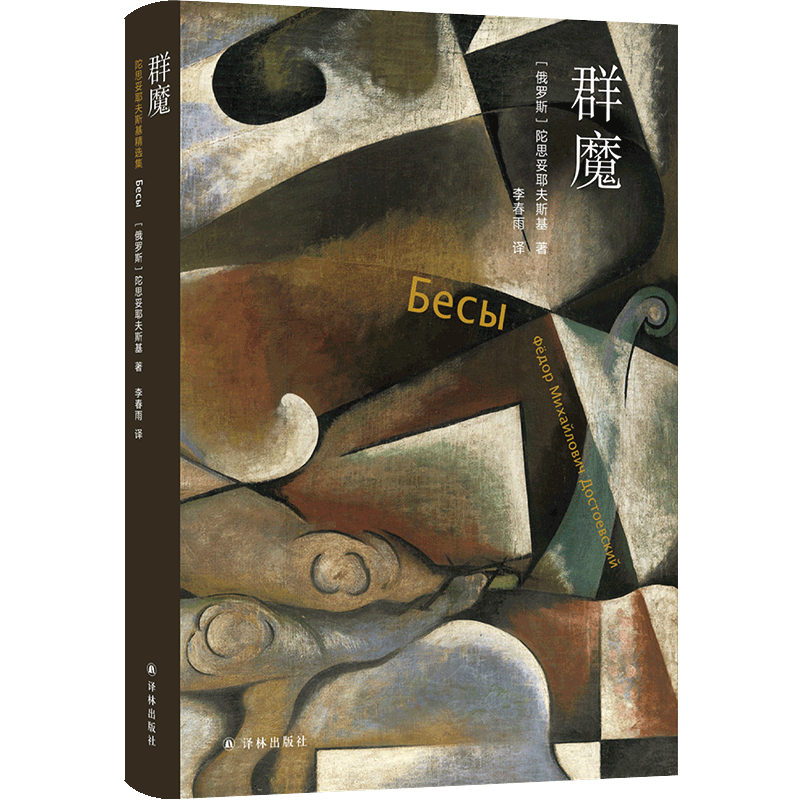
《群魔》
首先,是远和近的角度。在1860—1870年代的俄国语境里,《群魔》有高度的现实指向性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我们可以具体地看到他赞同什么、反对什么。但与此同时,《群魔》又是关于人类命运的整体隐喻。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作《脱离“土壤”的“群魔”——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的斯拉夫派立场》,研究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间的关系,将这部作品当作斯拉夫派观点的一个标志。我们会发现《群魔》与现实生活的联系非常紧密。其实在19世纪的俄国,有两位作家是这样写作的。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屠格涅夫。我们当然知道这两人是文坛上的宿敌,会用一些比较狠的语言来互相攻击。顺便说一句,《群魔》中的卡尔马济诺夫就是在影射屠格涅夫。陀氏在自己的书信中,也吐槽屠格涅夫如何娘娘腔,如何出尔反尔,等等。俄文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注释中,也会补充上这类轶闻,可见两位作家之间的矛盾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但他们之间存在分歧,其中一个原因是两人看待文学的态度、立场太相似了——两人写的都是身边事。托尔斯泰主要写的是历史,尽管《复活》是写当下,但你还是会发现作家与当下拉开了距离;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是高度抽象化、类型化的,他们笔下的故事可以平移到任何一个国家。但在19世纪的俄国作家中,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写的是俄国社会当下的事情。俄语中有一个词是“актуальный”,一般翻译为“现实的”“时效性的”“当代的”“迫切的”等,但我们其实一直没找到一个足够准确的中文词汇与之对应。这两位作家所写的就是“актуальный”的题材,就是我们身边的、需要被反映、被解决的问题。
加缪特别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群魔》中的人物“不能够爱,又为不能爱而痛苦”,还说他们“虽然有信仰的愿望,却又产生不了信仰”,这是双重悖论;加缪又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拒绝了不是社会主义的宗教,也拒绝了不是宗教的社会主义”。这三点就是加缪从《群魔》中读出的思想内涵。
我们在文学史上会说《群魔》是陀氏作品中最有现实指向性、最有倾向性的作品,作者总是忍不住要跳出来,摆他的立场,也就是反西方、反激进、反虚无主义的立场。但我想强调的是,更具有现实指向性的作品,往往也是对整个人类存在状态的巨大隐喻。近的东西,同时也是远的东西。我们今天的读者已经脱离了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社会,所以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作品中那些“远”的问题,比如信仰的选择、灵魂的痛苦,以及社会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大家要注意加缪在这里说的“社会主义”,其实可看成一种隐喻,看成一种集体主义精神。
俄国很多评论家在谈到《群魔》时,会强调它的主题是对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品的戏仿。陀氏写的是1840年代的虚无主义对1860—1870年代的俄国社会造成的危害,即所谓的“遗毒”。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说子辈会胜过父辈,子辈的实践精神、革命精神是要超越父辈的。但陀氏告诉我们,1840年代那一代虚无主义者的孩子们都不成器、堕落了,子不教父之过。《群魔》中的彼得和尼古拉·斯塔夫罗金,都可以看成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的儿子,一个是生理上的儿子,一个是他的学生,也就是精神之子。
《群魔》的第二种读法,就是要看到其中“维持平衡”的问题。后来的读者推崇这部作品,实际上是意识到一个事实:任何政治理想、宗教信仰,必然面临一个问题:在你获得信仰的同时,能否保持选择的自由?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等宗教哲学家相信,只有东正教是有选择的信仰,可以让人在不失去自我的前提下心悦诚服,由此解决信仰和自由的矛盾;另一个问题是目的和手段的平衡。我们可以为了一种公认的崇高、正义的目的,去剥夺任何一个人身上哪怕是特别微小的权利吗?陀氏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提到,整个天堂、全部真理都抵不上一个无辜孩子流的一小滴眼泪。这些段落到现在依然很感动我们。《群魔》中写到小组成员沙托夫,其实没有犯任何错,只是因为彼得要树立权威,就故意把他捆起来杀掉,沉到池塘里去。如果说五人小组的这种行动是为了实现人类的美好未来的话,大家会觉得,这个未来哪怕不要也可以。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写到的:我就不想要2+2=4,我觉得2+2=5也挺好。最后一点要保持平衡的,就是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夫人在回忆录中谈到,《群魔》是陀氏写得最累的一本书,后面写《卡拉马佐夫兄弟》都没有这么累。因为作者要取材于现实中的涅恰耶夫案件,但又不能写成廉价的报告文学。事实上,故事中三条线索彼此勾连得相当巧妙。尤其难的是加入了斯塔夫罗金的心路历程。斯塔夫罗金也是我们在俄国文学中谈论最多的。我们通常会把他和《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相提并论,因为在他们身上都反映着作者忏悔的心路历程。《群魔》的结构其实很好,但在关于这部作品的评论文章中,我们很少看到针对其形式的分析、艺术的分析。作品中的思想性内容遮蔽了它的形式。在阅读过程中,如何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之间维持平衡,也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这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历代评论家的偏差,对《群魔》这部小说艺术作品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
张猛:《群魔》幽灵在先锋艺术中的重生
我从20世纪20—30年代俄罗斯先锋派艺术文学的角度,来谈谈对《群魔》的理解。《群魔》中有两个人物代表了年轻一代,一个是尼古拉·斯塔夫罗金,另一个是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斯塔夫罗金”在古希腊语中应该是“十字架”的意思,十字架本身是一个规范,是正统、标准,但主人公的行为反映出一种矛盾性,让我们想到一个俗语:“会咬人的狗不叫。”他彬彬有礼,很有教养,通情达理,但他的脸就像一个面具。在他出场的时候,周围的人对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有的人特别崇拜他,有的人反对他,这两种相反的态度,就反映出了他的复杂性格。他永远不动声色,但又总是在启发周围的人,引诱出别人心中的魔性,否则他也不会成为所谓“五人小组”的精神领袖。与沉静的斯塔夫罗金恰成对比的,是狂热的韦尔霍文斯基,他永远躁动不安,说话快,走路快,带着挑衅,要把别人的情绪调动起来。这两个形象,一个是在平静中汹涌的暴力,一个是蛊惑人心的宗教领袖形象,两人其实有对位的关系,为文本赋予了张力。而沙托夫居于这两个人物之间,是一个被寄予了希望的新斯拉夫主义者,一个“根基派”。“沙托夫”(Шатов)这个姓氏,可能是来自动词шатать(摇摆、摇晃)。这个主人公的思想也是处于震荡、摇摆中的。这些主人公,以及整部作品,都带有强烈的精神震撼、矛盾冲突特征。
我在做白银时代诗歌研究时,读到一位学者的观点,说俄罗斯文学其实是有两条传统的:普希金,以及后面的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是一个流派,整体上是和谐的、阳光的,是建构性的、无所不包的,他们的思想是偏向理性和乐观主义的;而另一个流派是从莱蒙托夫开始的,他写过《当代英雄》,他的传统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继承下来,主人公是分裂的,故事是矛盾的,充满了流血和暴力,后来的安德烈·别雷、丹尼尔·哈尔姆斯,以及俄罗斯的一些现代派作家,如马雅可夫斯基等,就遵循着这样一条路线,他们构成了另一条支流,这里充满了对抗、矛盾、悖谬,具有一种怪诞的美学风格。果戈理在《死魂灵》中对人物的描写充满了戏谑、夸张、讽刺,这与托尔斯泰那一派所追求的理性的原则是不一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恰恰体现了这一种特性。《群魔》在刚问世时是被排斥的,但后来逐渐被接受,尤其是被大多数现代派作家所接受。未来主义作家马雅可夫斯基写过以“城市—地狱”为主题的诗歌,他的作品中,有很多关于打破后重建,或者纯粹关于打破的内容。就像未来主义者的宣言中提到“要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从现代主义轮船上扔下去”。未来主义者的风格就是歌颂冲突的。
我还要提到一位作家——安德烈·别雷,我几年前曾就他的小说《彼得堡》写过一篇书评。我们知道,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经常出现彼得堡形象,《穷人》《白夜》《罪与罚》等作品中的情节都发生在那里。这个城市的形象总是阴郁、黑暗的。而在安德烈·别雷的作品中,彼得堡神话又一次出现。《彼得堡》讲述的是1905年俄国革命前夕,包括贵族、平民知识分子、商人在内的俄国社会各阶层对于战争和革命的热望。与《群魔》相似的是,《彼得堡》中也有一个关于暗杀的背景,而且是用现代主义的手法描写暗杀过程。和《群魔》一样,主人公也是一对父子,甚至其中儿子的名字也叫尼古拉。他被要求用一枚装在沙丁鱼罐头里的*炸死自己的父亲。这个沙丁鱼罐头在他脑海中一次次爆炸,在他脑海中革命已经成功了,但事实上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个情节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有很多关联。康定斯基、爱森斯坦(《战舰波将金号》)、马列维奇等艺术家,也是在1920—1930年代的这个时期,以冲突作为艺术的来源,以“打破旧秩序”为主题进行创作。他们的创作都被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在现代的延伸,是20世纪上半叶时代氛围的集中体现。
我还想为大家推荐一部电影。2017年我写过一篇关于俄罗斯先锋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论文,他的《背叛》《盛夏》等作品都很有名。我想推荐的是他的《门徒》。在改编为电影之前,剧作的俄文译名为《(М)ученик》,是мученик(“受难者”“*”)和ученик(“弟子”“学生”)两个词的组合。主人公韦尼阿明从社会身份上看是学生,而从宗教意义上说又是门徒,是苦行僧和蒙难者。电影的内容与《群魔》有很高的相似度。韦尼阿明是一个中学生,没有父亲,母亲一个人把他养大。他疯狂迷恋上了《圣经》,把《旧约》中的信条倒背如流。他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不能接受人是由猴子变来的,在课堂上挑衅生物老师。他还有个跛脚的朋友,狂热地崇拜他。他便把这个朋友当作自己的信徒,传授给他一些信条。他还试图用耶稣的圣谕治疗朋友的跛腿,最后当然是没有治好。但他一直相信奇迹的存在,最后甚至因为这个朋友的背叛而杀了他。影片结尾,他为自己做了一个十字架,背着十字架走出来。这个人物与《群魔》中的主人公有很强的关联,可以看成是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和斯塔夫罗金的合体。在俄罗斯的文化信仰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形象——一个教条主义者,希望别人全心全意服从他?导演所表现的绝不是一个个案,而是在讲述一种危险的思想。既是对现实的反思,也是对宗教精神的反思。
李春雨:如何通过翻译再现陀氏的文字炼金术
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想到的可能就是那些长篇巨著,还有他汪洋恣肆的语言、排山倒海的气势。似乎他更注重宏观的布局,更注重思想性,以深邃见长,对于文字细节是不太在意的,但这其实是很大的误解。晚年回顾自己的文学创作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这样写道:“在我的整个文学生涯中,最令我开心的是,我也成功地向俄语中引入了全新的字眼。每当我在别的书刊里读到这个词时,总会感到异常的新奇。”由此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在意,而且以创造性地锤炼字词为傲,而他的作品也的确为俄语贡献了大量鲜活有力的俗语、谚语、名言警句。我今天就从一个译者的角度,从遣词造句的微观层面带大家领略一下陀氏的文字艺术。作为引入,我想先分享一些在阅读和翻译过程中令我印象深刻的例子。
之一个例子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余华老师的《活着》。小说开篇就讲到地主少爷福贵,年轻时吃喝嫖赌败光了家产,把父亲活活气死了。这时家里的长工跑来报丧,用了一个特别的字眼,说“老爷像是熟了”。为什么会用“熟”代替死?“熟”对应的是什么?“熟”对应“生”,而“生”又对应“死”,所以“熟”与“死”就构成了一种巧妙的同义替换。但更重要的是,这里蕴含着一种独特的生死观。小说最后福贵感叹,说人活久了,经历多了,就像梨子熟透,该从树上掉下来。我们看到,死亡在这里被描绘成了一个瓜熟蒂落的自然过程,它既不是世俗眼中阴阳两隔的绝对对立,也不同于佛家强调的生死轮回,而是一种生命能量耗尽,自然而然归于静寂的状态。也正是这种贯穿全书的近乎植物般的生死观,让我们在《活着》这部小说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撕心裂肺的生离死别之后,最后能得到一种生命的豁达感。这就是所谓“著一字而境界全出”。
第二个例子是我几年前翻译的一本书——格鲁霍夫斯基的《地铁2035》,这是一部废土乌托邦小说,背景就是核战争毁灭了地球,残存的人类龟缩于莫斯科的地铁,但依旧四分五裂,自相残杀。书里有一个特别残酷的场景:地铁系统爆发了饥荒,饥民潮冲击站台,统治阶层就架起机枪对着居民疯狂扫射。在描写机枪的时候,作家用了一个形容词。我们大家不妨想一想,如果让我们去描写这样一挺开火*的机关枪,我们会从哪些角度入手?我们可能会描写它的外观——漆黑的、黑洞洞的;也可能会去描写它的动作——震颤的、咆哮的、喷吐火舌的;它的声音——哒哒的、轰鸣的、震耳欲聋的;或者赋予它一种心理状态——疯狂的、残暴的、嗜血的、杀人如麻的等等。这些也都很形象,但是作家用了“кpoвoxapкaющее дуло”,直译过来就是“咳血的机枪”。我当时翻译到这里的时候,真是拍案叫绝。我们仔细品味一下“咳血”这个意象,它有动作感,用剧烈的、痉挛性的咳嗽动作来比拟急促的、颤抖的机枪扫射;它还有声音,用沉闷的、撕裂的咳嗽声来比拟令人心悸的“突突突”“哒哒哒”声;它还有细节,有视觉,这场*最核心的视觉元素就是喷溅流淌的鲜血,因为机枪喷射的不是*,而是鲜血;最后,还写出了一种绝症病人濒死与疯狂的病态心理。所以我们看“咳血的”这么一个形容词,就囊括了动作、声音、视觉、心理,完美契合了绝望而压抑的末日氛围。
第三个例子是我新近翻译出版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去年12月出版,收录于上海译文出版社“窗帘布”系列;今年4月份又出了“企鹅布纹经典版”。这部作品堪称旷世奇书,一共只有24万字,但布尔加科夫呕心沥血,整整写了12年,平均一天也写不到100字,其炼字之精可想而知。时间有限,我就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盛大的撒旦舞会》这一章,魔王处决了一名莫斯科的密探,在这名密探到来之前,魔王的侍从说了一句预告性的话,说“我已经在这……的静谧中听到了他的漆皮鞋的橐橐声”。这里我给大家两个选项,之一个是“棺材般的静谧中”,第二个是“像棺材里一样的静谧中”。大家可以选一选,觉得哪个更有文学性,哪个更好一些?我感觉答案是一目了然的,是前一个。为什么?因为“棺材般的静谧”更简洁凝练,而且意象鲜明,能够瞬间唤起我们关于死亡、封闭、绝对死寂的联想,精准地契合了撒旦舞会上那种诡谲阴森、非人间的魔幻氛围。关键是它超越了字面逻辑的束缚,以通感的手法将静谧这种听觉感受赋予了棺材冰冷封闭的恐怖之感。相比之下,“像棺材里一样的静谧”虽然更加具体,却稀释了直接的冲击力与文学韵味,就显得冗长而直白。原文是“в этой гробовой тишине”,“гробовой”就是由“гроб”(棺材)”构成的形容词,直译就是“棺材般的静谧”。布尔加科夫十二年磨一剑,值得我们在译文中去捍卫他语言的精准力量与独特的魔幻气质。
具体回到《群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用词是非常精准的,特别是在刻画人物的时候。对于小说中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就是父辈,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作家给他贴了两个标签,之一个是гражданин(公民),第二个是пятидесятилетний младенец(五十岁的婴儿)。гражданин这个词,直译是公民,但几位前辈译者都没有直译作公民,而都是翻译成“仁人志士”或是“爱国志士”之类,原因很简单,我们今天所说的“公民”,与19世纪政治语境中的“公民”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后者指的是带有进步、民主色彩的一类人。但在小说的语境中,它又并不是完全褒义的,而是带有反讽色彩,所以后来我把它翻译成了“公知”。可以看一下这个词出现的语境,例如,书中说韦尔霍文斯基“在我们中间一贯扮演着某种特殊的,怎么说呢,公知角色,并且对扮演这一角色极度热衷,我甚至觉得,不这样他就活不下去”。后面又说,“五十三岁哪里算得上老呢?然而,或许是出于公知做派,他非但不往年轻里打扮,反而喜欢倚老卖老,穿着那身行头,身材颀长,长发垂肩,俨然一位年高德劭的老族长”。第三处,“在最后的一次朗诵会上,他试图以其公知的雄辩挽回局面,幻想着听众的心灵能够被触动,对他的‘被驱逐’萌生敬意”。我们从这些字句中,可以概括出这个人的特质:表演型人格、装腔作势、夸夸其谈,以意见领袖自居。这正与我们现代语境当中的“公知”完全契合。
再来看另一个标签——说他是一个“пятидесятилетний младенец”,直译是“五十岁的婴儿”,但我们可以看到,前辈译者也都回避了“婴儿”这个字眼,而是翻译成“长不大的五十岁的孩子”,“虽然年过半百却还是一个孩子”,“年逾半百的最天真的黄口小儿”,“黄口孺子”等等。我的翻译是“五十岁的巨婴”。在使用“巨婴”一词的时候,我其实隐约预见到了可能会引发争议,后来果不其然,有些读者认为“巨婴”这个词太过新潮了。但我们想想,这个词是不是很符合这个人物的一些特质?他心理上幼稚,精神上不成熟,动不动就哭,一直接受一位女地主的豢养。作家把他比作这位女地主的一个“骨肉”“造物”“骨血”,说她像他的奶妈一样,等等。刚才刘文飞老师的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群魔》实际上是对整个人类存在状态的巨大隐喻”。从这个角度来讲,“公知”与“巨婴”标签贴在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身上,恰恰是很合适的——仿佛作家在当年就已预见到了我们现代人精神上的顽疾和通病。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是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巨婴式人物”之一。
接下来再讲一个例子,这是发生在两个子辈之间的一个情节。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听说斯塔夫罗金去跟人家决斗了,就非常气愤。因为斯塔夫罗金一旦死了,彼得就无法拉他下水,帮他搞革命叛乱了。所以彼得就跑来找他兴师问罪。彼得从后面追上来,不经意按住了斯塔夫罗金的肩膀。这个细节很值得注意,因为在俄罗斯的社交规范中,非必要的肢体接触会被视作对他人空间的侵犯,特别是在19世纪阶层有差别的人群当中,会被视为非常粗鲁的冒犯。所以斯塔夫罗金的反应非常激烈,他猛地甩掉彼得的手,转过身来对他怒目而视。这时彼得就瞅着他,露出了一个“……的古怪笑容”,但这一切只持续了一瞬,斯塔夫罗金就转身走远了。作家在这里用длинная(长的)来形容 улыбка(笑容)。длинный(长的)是很常见的形容词,我们通常用它来表示时间和空间上的长度。前辈译者他们是这样翻译的:“久不消失的古怪笑容”“久久的、凝固的古怪笑容”。但这样翻译明显与后面“但这一切只持续了一瞬”是相互矛盾的。也就是说,длинный在这里只能理解为空间上的“长”,我起初想翻译为“长长的”,但这样可能还是会被理解为时间的“长”,而且“长长的”是一个叠词,在汉语中就自带一种抒情意味。我又想译为“扯到耳根的古怪笑容”,这样虽然具象化,但又显得夸张了。最后我还是尽量贴近文本,译为“拉长的古怪笑容”。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表达?这样的笑容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心理?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超的心理描写技巧,他用一种表情来揭示非常隐秘的心理。如果读过小说,我们就会知道彼得对斯塔夫罗金的情感和态度是非常复杂的,他既惧怕他,又想控制他,他搭他的肩膀,显然是有意冒犯;但他又要做出一副不经意的样子来掩盖自己的真实企图。面对斯塔夫罗金的发怒,彼得其实是心虚了,想讨好,但又不愿过分示弱,所以要假装强硬,这才有了这样一种“拉长的古怪笑容”。这是一种没有真实情感、没有弧度的、僵硬的、硬扯出来的、皮笑肉不笑的笑容。你如果去仔细揣摩,就会发现,在一个看似简单的形容词背后,其实隐藏着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人物心理描写之深的表现。但是这些都隐藏在文本当中的字里行间,需要我们去仔细揣摩。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有很多精妙的用词,比如我们刚才说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有表演欲,作家写他在准备演讲之前,站在镜子前“忙着试戴各种微笑”。作者的原文就是“примеривал”就是指试穿、试戴各种衣服、鞋子、帽子等。我们平时试穿各种衣服,是为了看看效果,而作者写他换上各种笑容,也用“试戴”,就非常巧妙。还有,讲到火灾之后,“终于等来了愁云惨淡的黎明。火势渐弱;风停之后突然一片阒寂,接着下起了小而慢的雨(мелкий медленный дождь),像是用筛箩筛下来的”。这里的“мелкий медленный дождь”当然可以译为“毛毛细雨”,但我个人觉得,“小而慢的雨”的表达更精确,也更新颖。
最后再讲一个例子,也涉及对原文文化意象的传递。原文描述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感觉对省长连布克的拉拢还不到位,“надо еще поддать пару, чтобы польстить и совсем уж покорить «Лембку»”(直译:“需要再加些蒸汽,以便讨好‘连布卡’,甚至彻底征服他”)。这里的“поддать пару”是一个习语,源自俄式 *** 习俗——向灼热的石块泼水,瞬间蒸腾起大量热气,比喻“加大力度、火上浇油”。此处的翻译难点在于:如何在传达“加码施压或讨好”这一意思的同时,自然保留原文中的独特文化意象。臧仲伦先生采用归化策略,译为“必须再加把劲”,舍弃意象以求流畅;冯昭玙先生尝试部分保留,译为“需要再加点温才能拍上马屁”,但读来稍显牵强。我的译文是:“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呢,大概觉得这还不够,还得往 *** 室里再加点热气儿,好让‘连布卡’蒸得更舒服些,彻底‘征服’他。”如此处理,旨在不添加译注的前提下,让俄式 *** 的文化意象自然融入中文叙事,精准传递彼得步步紧逼、意图以“氛围热压”降服对方的心思。此外,译文中的“蒸得舒服”与“征服”暗含谐音关联,强化了意图与目的的契合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