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兰察布市的蒙古包,探亲途中拍摄
在那个1块钱能吃半个月的年代,三十多元钱无疑是一笔巨款,家里人也终于松了口,没再多问。
1965年3月,泸州货运站弥漫着煤灰与露水的腥气。1960年代的泸州并未开通客运列车,研究所的全体人员和仪器都只能通过货运列车抵达内蒙古。车厢焊死了所有窗户,只在顶棚留两排拇指大的气孔。带队的排长扯着嗓子吼:“保持间距,人货混装!”研究人员与各种仪器共享空间。谢方夏蜷在军用列车尾厢的仪器箱隙间,她的行李很简单:“红五类”政审证书、三套新衣服、一罐母亲做的辣椒酱。新入伍的5名学生被编为S75至S80号,她是S76——这个编号将取代姓名使用35年。
到达内蒙古,掀开车厢门那刻,风沙就劈头盖脸砸来。等待军用卡车前来接洽的时间,她和初来乍到的同事们眯眼望着无垠的昏黄,好友拉了拉她的袖子,低声说:“棺材!那是运棺材的车吗?”谢方夏顺着好友的目光看去,六口刷着绿漆的松木箱堆在月台上,箱体印着“精密仪器”。多年后她才知道,那是为万一猝死技术人员预备的——因保密条例,遗体需与设备同箱运回北京,结束保密后才能通知家里认领。
基地位于荒漠地区,周围没有村庄。谢方夏住进了内蒙古研究所原有的单元楼里。从窗户向外望去,附近只有八栋六层楼高的住宅楼。
研究基地离住宅楼大约步行半小时,但最难捱的是四五月的风沙天气。
1966年一场巨大的沙尘暴袭来,当地人叫这样的天气为“牛毛风”。那天钢电工研究组工程组测试项目,需要使用进口仪器,任务紧急,仪器又只有她能熟练运用。谢方夏只能和同事们前往工作。大风卷起黄沙,真像牛毛一样,黄色的,粗粝的,整个天空都是落日一样的橙红色,她走在黄沙里,能见度不足五米。
晚上七点多,研究所只剩测试结束后的几人,她和几位同事一起下班,结伴回去。出门一片昏黄,路全部被“牛毛风”吹起的黄沙掩埋,全副武装的几人穿着四五层衣服,戴着防风面具和护目镜,手挽着手,只能靠记忆中的方向往住宅区靠。狂风卷起拳头大的石子,就要砸在谢方夏的帽子上,她抬手抓住,放进了口袋。现在这块石头也和那五本荣誉证书一起,保存在了抽屉里。“可能是能够被允许留存的东西太少,我又太想记住。”她在日记里这样解释道。

内蒙古沙尘暴,相较“牛毛风”能见度较高
半小时路程,几人走了两个小时才终于看到了光亮,听到了呼唤他们名字的声音。原来是研究所领导发现几人还没回来,每半小时派出一拨人去寻找,直到第三拨人才找到风沙中走出来的他们。
谢方夏的工作是操作员,按照技术员的实验配方完成相关步骤,并记录在工作日志上。由于保密工作需要,每位研究员的工作日志都需写两份,当日收缴,进行模糊处理。
工作并不容易,谢方夏要面对技术操作的难度、生活环境的恶劣,还要承受“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压力。实验失败造成的损失太大,任何一个人都没法承受,她只能谨慎再谨慎,至少保证不是她这一环出现失误。
在谢方夏35年的工作生涯里,“保密”二字已经刻进她的骨髓。除了自己参与的项目外,系统内不允许同事间相互交流,更不能去别的科室串门。每一层楼都有 *** 站岗,拿着“*实弹”巡逻。
刚到内蒙古基地的一个月,不允许与家里人联系,信件中更不能提到与工作相关的任何地点与要素。谢方夏寄给家里人的信,会被拆开审了又审,才会和她省下的薪水一起寄回四川,连同寄出的还有她为了做戏做 *** 托后勤购买的几支全新牙膏。
一次操作中,实验药剂性能突变腐蚀了手背,她在工作日志上如实记载了这一情况。下班交上日志后,科长递来半瓶修正液:“凡涉及具体操作的句子全涂改掉。”她看着自己的笔迹消失在白色涂层下:“在……中因化学物质变异导致谢方夏……”改成了“特殊工况下出现……”
涂改液凝结成痂片时,窗外响起运输车的轰鸣。三辆覆盖帆布的卡车正驶向铁路专线,车厢里装着谢方夏曾经参与项目的完整档案——那些写满人名的原始记录将永久封存在某个保密山洞里,洞口浇筑的混凝土标着“xxxx号机密”。而留给保密工作人员的,只有一本本具体内容不能公布的荣誉证书。

四川泸州,谢方夏从小生活的老家院子(修缮前),她生病时在此康养
20世纪7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国家实行以加强国防为中心的战略大后方建设,要求北方各军用工业基地向南方迁移。
1970年11月7日深夜,上级发布“战略转移”,内蒙古基地所有研究人员与实验设备需迁移至湖北山林。谢方夏用哺乳巾将三个月大的儿子捆在胸前,后背绑着火箭的陀螺仪保险柜,和丈夫搀扶着行进。孩子营养不良,轻飘飘的没什么重量。十五公斤的钢柜压得她椎骨脆响,导致现在她的腰椎都存在畸形。
几次辗转,研究所进入湖北深山,实验室建在峡谷里,从进山到实验基地几乎要走一天时间。夜里很冷,谢方夏和几位同事每天背着孩子上山捡柴火,捡了,往下一滚一扔一滚,另有同事在下面接应,集中分发。谢方夏11年的日夜都在湖北这个说不出名字的山沟里,日复一日重复着生活与工作。
山里的生活环境比内蒙古的黄沙还恶劣,地理原因导致白天很短,夜里没暖气,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天气只能靠一层一层的被子和衣物扛过去,原始森林里还有老虎和狼出没。夫妻二人的任务也一天比一天紧急,无暇照顾体弱的儿子。1974年春节将至,二人与组织沟通,决定将刚学会说话的儿子连同年货一起送往四川外婆家,委托列车员照看。谢方夏向家里解释的理由是孩子不适应工厂环境,加上到了上学的年纪,就请大哥帮忙照顾。
但悲剧发生了。那时候的信件总是延迟,谢方夏收到儿子走丢的消息已经是一个月后。大哥寄来的信中写道:“腊月初八接站,广播喊了整天孩子的名字,没见到人,怀疑中途下错了站。”随信纸寄来的还有派出所出具的《走失证明》,报案人签名处按着大哥的指纹。
在那个没有监控的年代,想找到一个孩子无疑是大海捞针。走丢孩子基本就是永生难见。极大的打击下,谢方夏的身体再一次垮了,病危通知书送到陪床丈夫手里。愧疚,心疼,她躺在病床上想:要不就这样死掉算了。她不知道应该怪谁,但总有人需要对这个悲剧负责。那就怪自己吧!谢方夏忍不住哽咽,直到五十几年后的今天她仍然这样想。
好在上级对此极为重视,派了专员在途经站附近寻找,几经波折,终于找到孩子,送回了四川老家。家乡的信寄来,大哥写道:儿子身上全是伤,问起经历只一味地哭,哭累了就盯着家人,也不爱说话。孩子到底怎么走丢的?没有人知道。夫妻二人心疼,着急,但能做的也只有多省下点钱,寄回给家里——项目正是关键时刻,不允许离开岗位。同一年,母亲去世,谢方夏也没能回川吊唁。
夫妻二人再次见到儿子已经是20年后。工作缓和的二人带着十多岁的女儿回到了四川老家,几天前,大哥去世了。小院里的枇杷树下,二十多岁的青年被亲戚拉扯着站在夫妻二人面前,扭头就想走。“是我对不起他。”谢方夏谈起儿子就哭。青年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他的五官与夫妻二人很相似,但对于他来说,自己是这个家的“外人”,是被抛下的一位。他记忆中不愿触及的伤痛,都来源于眼前的两位老人,他做不到释然,甚至连联系方式都不想留给他们。
女儿生于1979年,刚出生就被确诊佝偻症,头像鱼一样又宽又扁。
这种畸形在医学上被称为“舟状头”,病理名称又称颅缝骨化症,是由于先天发育障碍所致。佝偻病在婴儿期较为常见,是缺乏维生素D引起体内钙、磷代谢紊乱,而使骨骼钙化不良的一种疾病。
谢方夏只能一遍遍在日记上写下“对不起”,她并不知道哪里错了,但后果总需要有人承担。夫妻二人又开始为女儿的病情奔走,好在检查结果乐观,都只是因为孕期营养不良导致的畸形。终于在两次手术和几年的治疗后,女儿的身体基本恢复正常,但体质偏弱,发育也较同龄人迟缓。
闲暇时,一家三口去各地旅游,爬过黄山、泰山,去过高原。走过最远的地方是韩国,材料申请审批了一个月才通过。走过的全国大大小小五十多个城市,全在客厅中挂的世界地图上标注出来,合照先是3人,女儿结婚后成了4人,有了孙女变为5人。但旅游目的地没有湖北。谢方夏不愿意谈理由,“我闭上眼就会想起来儿子盯着我看的眼神,跟看陌生人一样。”她又开始道歉。
谢方夏很喜欢看史铁生的书,在基地时她就常去文献部借阅,放在床头看。退休后,她的日记和史铁生散文集一起放在书架上。日记的扉页写着:“工作的记忆,不允许被留下,那痛苦为什么无法遗忘?”下面摘抄了史铁生《务虚笔记》的话:“‘忘记’这两个字能使一切珍贵的东西消灭,仿佛不管什么原本都一钱不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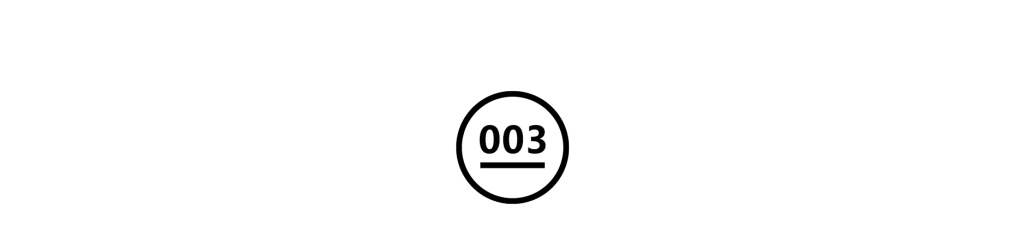
她的名字,代号S76
2000年10月初的一个上午,内蒙古实验基地的后勤部,谢方夏正在办理退休手续。小窗后递出一张建设银行存折。上面新打印着字样“月退休金4376元”,下方几条横线划掉了一排字,仔细看能辨认字迹:“保密津贴:1200元”。她询问起原因,财务人员解释:“解密人员不享受保密补偿。”
她还是很开心。家里的经济早已没有了重压——丈夫没到退休年龄,女儿也有了家庭,小夫妻二人都有稳定的工作,还生下一个健康的女儿。
军用客车把谢方夏送到最近的县城,她感受着周围的人烟味,又顿感迷茫:35年每天都在和操作台作伴,世界好像变样了,应该要干什么?她脑子里只剩一个词:回家。她搭乘大巴来到了女儿所在的呼和浩特市,这是退休流程的最后一步,在省公安厅做解密报备。保密科内,钢印重重压下“解密期三年”的备注——三年内她不允许擅自离开内蒙古,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向公安系统备案。
处理好一切,她攥着存折走向百货大楼,在羊绒专柜前徘徊了很久。最终,她买下一件一千多元的暗红色大衣和一件同款的灰色大衣。暗红色的长款大衣穿在了女儿身上,正好合身。灰色大衣至今没能寄给它的主人,因为儿子的一切信息都无从得知。
他住在哪里? *** 多少?孩子几岁了?一家人过得怎么样?没有人能够回答她。那位青年在谢方夏大哥去世后,与所有亲戚断了联系。这件灰色大衣带着81岁老人洗不掉的愧疚,永远锁在了衣柜的最上层。
退休生活很丰富。谢方夏爱上了做饭,尤其爱做川菜,仿佛遗失在记忆里的故乡,都能通过美食找回来。她每天按时接送孙女上下幼儿园,其余时间就收拾家里,准备三餐。
孙女喜欢乐高,谢方夏的退休金每月总有一部分花在上面。她也很喜欢这种玩具,可以找到操作台的感觉。她拼起乐高来又准又快,总能得到孙女的赞叹,她笑着说:“孙女都成我的‘小粉丝’了。”
她还加入了老年协会,成为了副会长,周末与会中同伴一起骑行、散步。她常组织老伙伴们骑行郊外,在晴朗的天气里,沿着大青山脚缓行。与记忆中内蒙古基地那遮天蔽日的黄沙不同,近年来植树造林,大青山植被茂盛,风沙也温和很多。偶尔,她会独自骑得远一点,望着无垠的草原或城市的轮廓。她喜欢骑行的感觉,因为前半生的方向都跟着墨绿色的军用车行进,现在终于能自己选择东西南北了。
谢方夏与四川老家的亲人恢复了联系,加入了“欢乐一家亲”的微信群。但她很少回四川,只逢年过节在群里聊聊。
2024年的国庆,她邀请亲人们来呼市玩耍,这也是大哥在世时没能完成的愿望。谢庆良想替父亲来看看这位传奇的小姑生活了五十多年的地方。谢方夏跟大家聊内蒙古的风沙、聊曾经不能说的荣誉、聊退休后的生活,唯独对那三十五年的具体工作,依旧守口如瓶。
展示过后,谢方夏拉开那个陪伴多年的旧抽屉,将荣誉证书放回最上层。证书下方,压着那块从1966年“牛毛风”中拾回的拳头大的石头。旁边,是一份“集体三等功”的奖状复印件,那颗返回式的卫星带来的荣誉,如今只剩下这张黑白复印的纸,上面能找到的她的存在,是批注行的参与人员编号,其中就有S76。她的名字无法完整留存其中。
客厅里,那幅标记着五十多个城市足迹的中国地图依然醒目。只是湖北那片区域,始终是地图上一个沉默的空白点。
欢迎继续关注本期“小行星计划”专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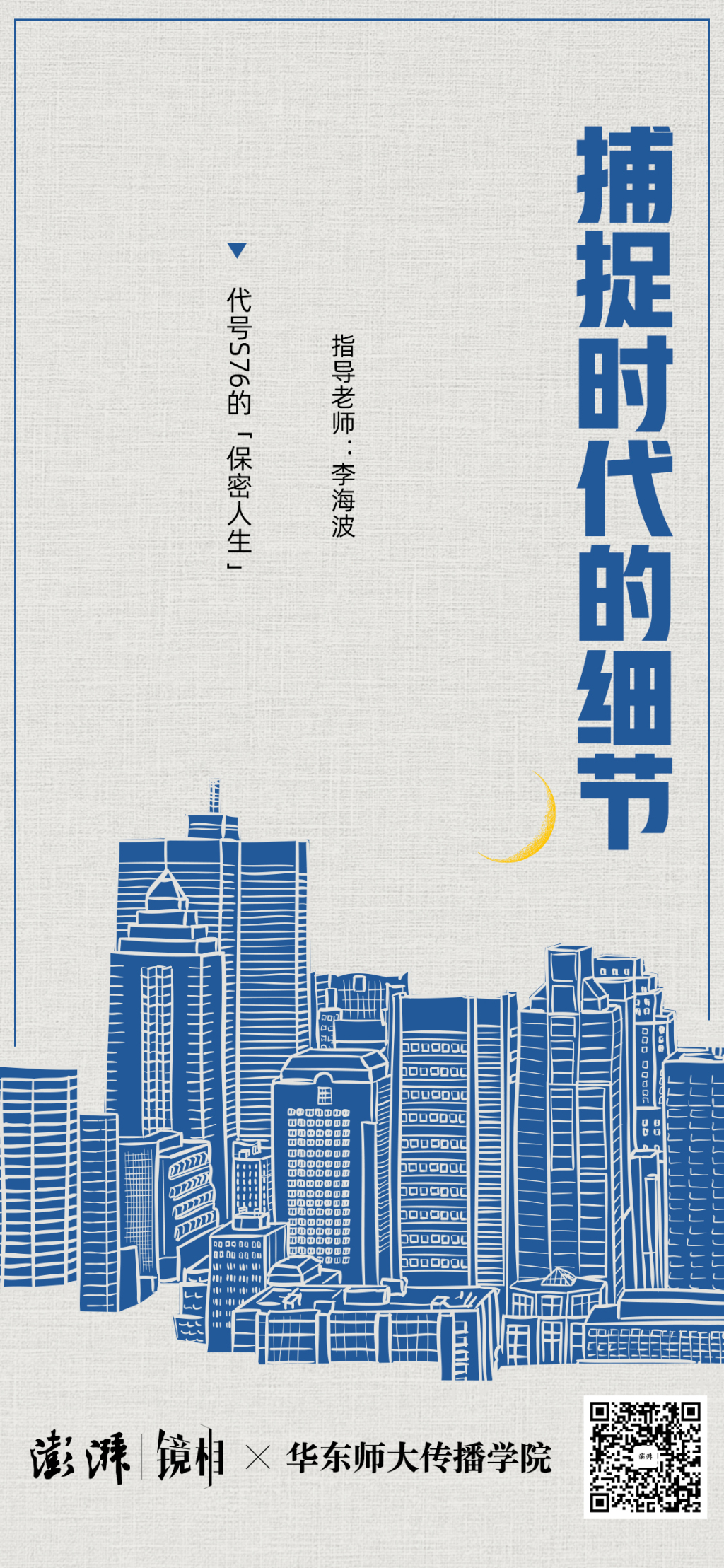
海报设计:周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