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赖堡跟随胡塞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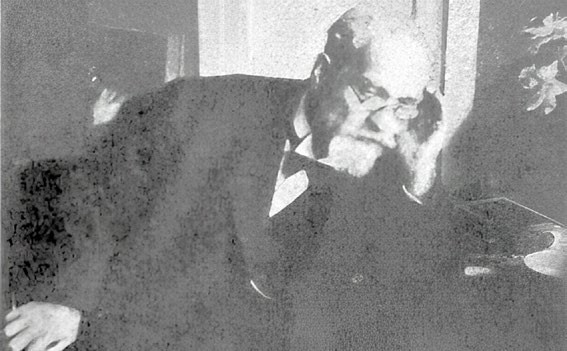
胡塞尔教授在倾听
一九一九年年初,当我在极恶劣的政治动乱中离开慕尼黑,搬到弗赖堡时,我在慕尼黑的老师亚历山大·普芬德与莫里茨·盖格尔把我推荐给了胡塞尔。胡塞尔在一九一六年接下李凯尔特(Rickert)的位置,从那时起,他不但成为弗赖堡大学哲学系的核心,实际上也成为整个德国哲学的焦点,许多外国学生为了他来到弗赖堡。他那种巨匠风范的现象学分析、冷静而清晰的演讲、人性化却又严格的科学训练方式,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成长,也给我们指出现象之不受时间局限的“本质”(Wesen)——这本质立于转瞬即逝的现实之外,他用数学与逻辑的存在当范例来掌握之。他强迫我们在讨论课的演练里,避免使用一切伟大的术语,要我们把每一个概念都用对现象之关照(Anschauung)来加以检验,然后在回答他的问题时,不要给他“大钞”,而要拿出“零钱”来。他正是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所描述的“精神的良知”(Gewissenhafter des Geistes)。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许多人担忧法国部队即将占领弗赖堡的那些日子里,大学的讲堂变得冷清不堪,而这位对最细微事物的伟大研究者,是如何用比平日更安详与坚定的态度,继续讲述他的学说——仿佛科学研究纯然认真的精神,不可能受到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干扰一样。我们对胡塞尔的《观念》最不感兴趣的部分,就是他“还原超验意识”的学说,然而这也正是我在1933 年有机会认识其伦理源头与效力之处:胡塞尔在弗赖堡教学与著述了数十年,但是在纳粹党人政变成功之后,这个场域对他来说实际上就像被“置入了括号中”(in Klammern gesetzt),并不对他的哲学意识构成阻碍。虽然他那时已经退休,国家仍然将他再度停职,把他的作品从图书馆里清出来,标示为犹太作品,在一个“耻辱之柱”上公开展示。尽管弗赖堡大学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胡塞尔才得到当时的声望,校方却用完全漠视此事的态度来避免一切尴尬。一位格伦斯基(A. Grunsky)先生接着写了一本小册子,用意在证明胡塞尔,就像斐洛与科恩已经做过的那样,将“雅利安人”柏拉图式的观念世界染上了《塔木德经》的色彩。

胡塞尔在弗赖堡大学的研讨班,19020年
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的最后一次会面
1933 年,我最后一次到弗赖堡的那两天,去听了海德格尔的讲座课,他正在分析沉默有哪些不同的方式;他自己是最懂得沉默的人。他请我到他家里吃晚饭,他太太不在家。我们的谈话避开了一切难堪的话题,主要只讨论了我是否应该放弃马尔堡,把握机会转到伊斯坦布尔。他说我可以在他家过一夜,但是我没有接受他的好意,表示要住在一位昔日的大学同学、当时已是医学院讲师的家里,他听了似乎有点讶异。第二天我拜访了胡塞尔。海德格尔已经跟他完全断绝了来往,而且自纳粹政变以来,再也没有在他这位“如父亲般的朋友”(从前他在给胡塞尔的信上都这么称呼他)的家里出现过。胡塞尔仍温和而镇定地、深深地沉浸在自己的工作里,但内心却因为这位昔日门生的行径受了打击,而这位门生之所以能接任自己在弗赖堡的哲学讲座教授的位置,还是出于自己对他的提拔,现在这位门生更是当上了大学的校长。
我一九三六年在罗马时,海德格尔曾在那里的意大利与德国文化中心发表一场关于贺尔德林的演讲,演讲结束后他跟我回到了我与太太的住所。当他看到我们住处的设施如此简陋时,明显地露出了震惊的表情。他特别遗憾没能看到我的藏书——那些书都还留在德国。傍晚时我陪他回到他在赫兹(Hertziana)图书馆下榻的房间,他太太用一种友善但僵硬的表情,淡淡地跟我打了招呼。她大约感到难堪,因为她记得我从前是多么频繁地在她家里做客。意大利与德国文化中心的主任请我们到“炖小牛膝”餐厅用晚餐,席间避开了政治的话题。
次日我们夫妇与海德格尔、他太太、他的两个儿子——他们小时候我常常抱他们——一起到弗拉斯卡蒂(Frascati)与图斯库伦(Tusculum)郊游。天气晴朗而耀眼,尽管心里有一些难以回避的障碍,我仍为这次最后的相处感到高兴。海德格尔即便在这样的场合里,也还是没有把纳粹党徽从他的外套上拿下来,他在罗马停留的全程都带着党徽,也显然完全没有想到,如果他要跟我共度一天,配戴这纳粹十字章并不适当。我们聊着关于意大利、弗赖堡与马尔堡的话题,也谈到一点哲学的题目。他很友善,也很仔细聆听,可是跟他的太太一样,完全避免谈到德国的情形以及他的立场。在回程的路上我试着让他对这些政治问题坦诚地发表一点意见。我在谈话中提到了《新苏黎世日报》上的论战,也对他明说,我既不认同巴特对他所做的政治抨击,也不同意施泰格为他所做的辩护,因为我认为,他之所以选择支持纳粹,原因是深植于他的哲学本质之内的。海德格尔毫无保留地表示同意,并且对我解释,他的“历史性”的概念正是他“投身”于政治的基础。他也表示他对希特勒的信仰是不容怀疑的;他只低估了两件事:一个是基督教教会展现的生命力,另一个是兼并奥地利所遭遇的阻碍。他跟从前一样确信,纳粹对德国来说是通往未来的道路,只是我们“坚持”的时间必须要够久。他唯一忧虑的只是,那些过度的组织与动员是在消耗活生生的力量。可是对这整个运动所具有的毁灭性激进姿态,以及所有那些“乐力会”的狭隘中产市民性格,他并不觉得有何不妥,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激进的狭隘中产市民。我对他指出,我虽然对他采取的态度大多都了解,但是有一点例外,那就是他竟然有办法跟施特莱彻这样的角色同桌共餐(在“德国法学会”大楼里)。他听了之后先是沉默以对,然后终于还是不情愿地端出他著名的辩护理由(巴特在他的《今日的神学存在》里对这些辩护理由做了很棒的整理),主要的意思是说,要不是至少有几个了解状况的人进场关心的话,一切还会“更为糟糕”。他结束这番解释时,露出一种对那些“有教养的人”的尖酸怨恨:“假如这些先生没有自觉优雅以致于不肯投入的话,情况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可是实际上却是我一个人在那边孤军奋战。”我回答他,可是一个人并不需要特别“优雅”,就会知道应该拒绝跟施特莱彻合作。他则说:施特莱彻不值得我们为他浪费口舌,《冲锋者》杂志跟色情杂志简直就没两样。为什么希特勒不摆脱这个家伙的纠缠,海德格尔说他也不明白,或许希特勒有点怕这个人。这是一种典型的回答,因为对德国人来说,最容易的就是在理念上激进,可是对一切事实层面的东西无所谓。他们有办法忽略一切个别特殊的事实,以便能更加坚决地拥抱整体的理念,并且把“事物”与“人”分开来看。事实上那份“色情杂志”所策划的,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已经毫无保留地被完成了,已成为德国的现实情境,而且没有人可以否认,施特莱彻跟希特勒在这一点上是意见一致的。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
我把我写的论布克哈特的书寄给他,但是从来没有收到过他只字片语的道谢,更不用说有什么针对内容的评论。一年以前我把刚出版的论尼采的书寄给他,也一样没有回应。我还曾经从日本写过两次信给海德格尔,之一次是为了与他本人有关的、将《存在与时间》译成日文的事情,第二次是为了我临时需要使用几本从前在弗赖堡送给他的较罕见的书。这两封信他都是沉默以对。就这样,我跟这个人的关系终告结束,这个在一九二八年让我(他在马尔堡之一个也是唯一的学生)完成就职论文的人。
一九三八年,胡塞尔于弗赖堡过世,海德格尔证明他对老师的“尊崇与友谊”(这是他一九二七年把作品献给胡塞尔所用的献词)的方式,就是没有费心表示过一句纪念或哀悼的话——或者他根本不敢。公开与私下的场合都没有,口头与文字上也都没有。同样地,那位贝克尔——他从就职论文一直到获得波昂大学的聘书,也就是说他整个哲学的“存在”,都受到胡塞尔对其提拔的恩惠——回避这个难堪处境的办法,一样也是毫无表示。他的理由很“单纯”:他的老师是一个被解职的犹太人,而他却是一个担任公职的雅利安人。这种英雄气概,从希特勒掌权后就成为德国人常见的行为方式——如果他曾受到一个德国犹太人的提拔才获得现在的职位的话。很有可能海德格尔与贝克尔觉得自己的行为只不过是“诚实的”与“理所当然的”,因为在他们尴尬的处境里,还能够做些什么别的呢?
【本文节选自《纳粹与哲学家:一个人的流亡史》,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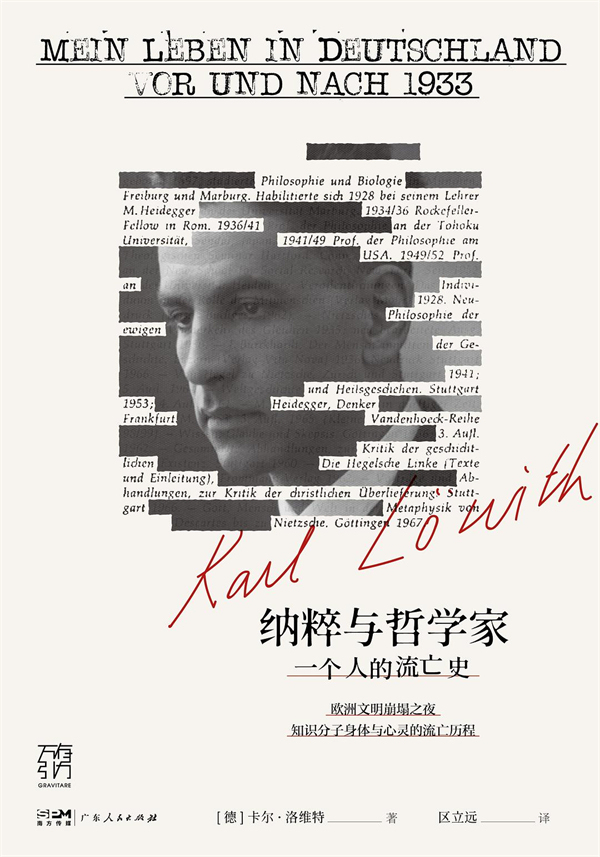
《纳粹与哲学家:一个人的流亡史》【德】卡尔·洛维特/著 区立远/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5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