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喜、科大卫《秘密社会的秘密:清代的天地会与哥老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虽然只有十万字,却可能是清代会党史研究划期的著作。无论是观点还是思路,该著都在重构以往的研究叙事。稍微熟悉这一领域的学者,很容易就能感到该著带来的冲击。说“可能”,是因为这些新观点需要学界更广泛的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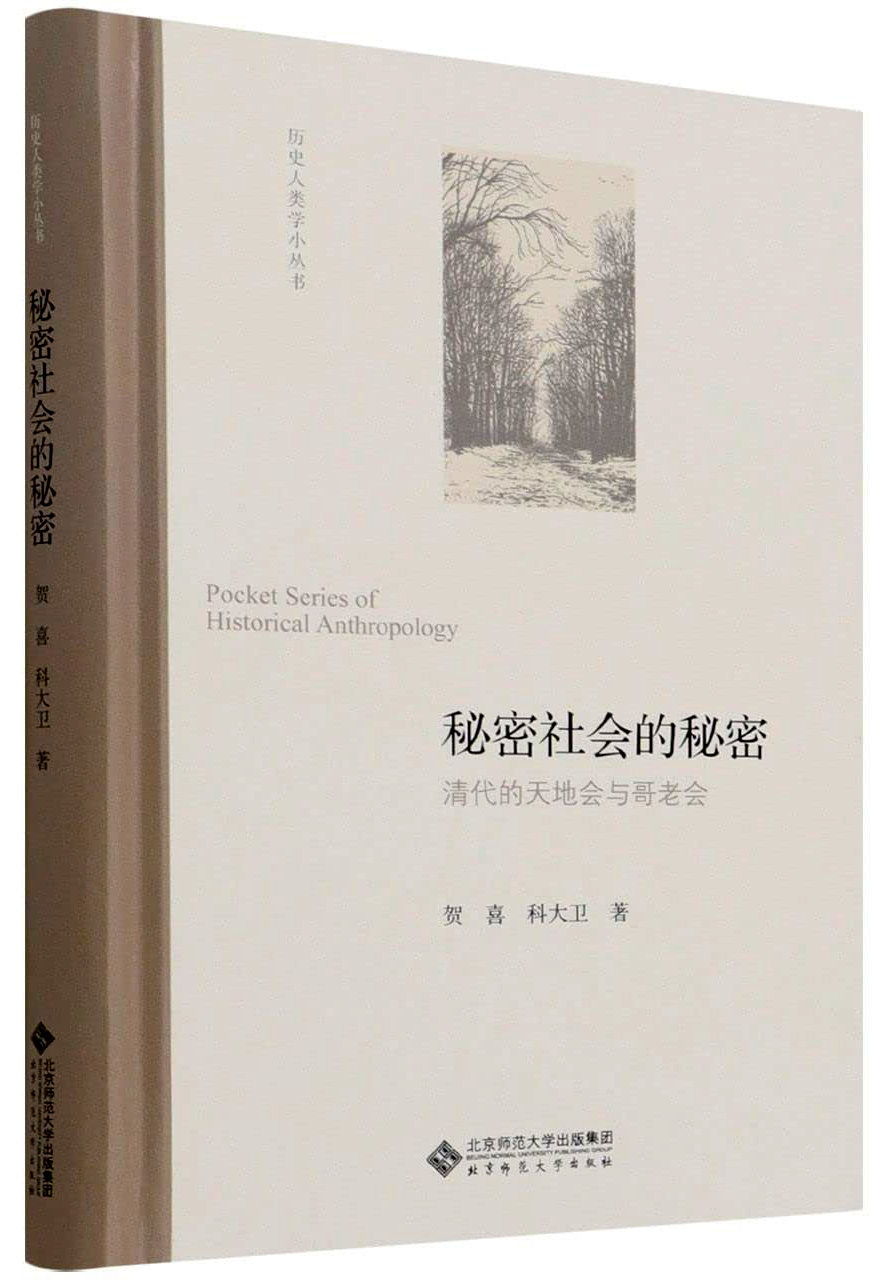
《秘密社会的秘密:清代的天地会与哥老会》书封
如书名所示,该著核心目的是揭示“秘密社会的秘密(特别是天地会和哥老会)”,但其具体论述关涉到会党史研究几乎所有重要问题。本文先讨论相关问题,最后再回到著者的核心观点。
一、走出天地会的起源
天地会的起源问题,是会党史研究中争论最多的老问题。著者开篇不久就指出,天地会起源于何时、何地,对参与拜会者来说,并不太重要。与其他结会相比,天地会独特的部分在于拜会是拜天地会故事中的祖师。这是个反对朝廷的论说,因此很多人自然知道拜天地会犯法,“可见,历史学者需要解决的不是‘起源’的问题,而是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明知故犯”。(18页)
虽然著者认为起源问题不太重要,几乎未做讨论,但如此多的前辈学者投身起源研究,不仅是出于好奇,更因为起源问题关系到天地会的性质,由此关系到天地会历史的叙述方式,因此有必要稍做回顾。
大致来说,围绕起源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
自清末革命领袖陶成章以来,不少人认为天地会是反清复明的组织,成立于康熙十三年(1674)。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天地会内部的各种传说以及会簿讲述的故事。故事内容大概是:康熙年间,少林寺一百二十八个和尚,帮助朝廷平定“西鲁番”之乱,结果没有得到赏赐,反而受奸人陷害,官兵火烧少林寺,只有五个和尚成功逃出。他们走到某处海边,发现一只白香炉,底部写“兴明绝清”,于是他们发誓联同徒弟,成为天地会的五房,五房在各省开枝散叶,为日后的活动做准备。(第9页)学者们努力将会簿中的各种情节对应到实际历史之中。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天地会是破产劳动者的互助组织,特别以蔡少卿为代表,1964年,蔡发表《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依据清 *** *林爽文起义档案中口供等材料的记述,认为天地会起源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两种观点的差别十分明显,由此讲述的天地会历史,起点便大不相同。
近年来,李恭忠尝试跳出这两种解释路径,其在2016年发表的《蒙冤叙事与下层抗争:天地会起源传说新论》中仔细排比了七种已知的天地会会簿,发现“只有早期的两部会簿以明朝灭亡、遗下太子作为故事的序幕,似乎暗示着天地会的缘起与朱明王朝之间有着某种渊源。但后来的会簿却断然放弃这一序幕,意味着天地会的缘起跟朱明王朝之间无需任何瓜葛”。由此,李恭忠重新理解故事本身,认为天地会传说实际是一种另类的“义士蒙冤”叙事,这种叙事采用了戏剧化的结构,清楚表达“蒙冤—怀恨—报仇—造反”的下层抗争逻辑。
李恭忠的看法富有新意,但似乎有一个 *** 上的小瑕疵。他试图“从歧异的具体细节背后整理出共同的叙事模式”,即把天地会传说看作故事,继而分析故事类型。故事类型分析的精髓在于共时分析,即不考虑时间因素,直接从不同叙述中抽绎出情节基干。“明朝灭亡”的情节并非情节基干的必要部分,因此,李恭忠的结论无视时间也能成立。考虑时间,反而带来两个新的问题,其一,实际上并不能准确判定会簿的时间;其二,保留下来的会簿与实际存在过的会簿比例悬殊,不能肯定之后就再没有出现过有“明朝灭亡”情节的会簿,由此勾勒出的时间线索只是一条虚假的线索。这也许显示历史学者思考问题的惯性。
天地会的起源问题至今没有定论,也不太可能有定论。如果按照旧叙事思路,这一问题似乎仍不得不提。不过,著者转换思路,很干脆地摆脱了这个老问题,这一点,放到最后再说。
二、叛乱的 *** 过程
由于史料存留状况影响,今天能看到的史料,无论是天地会、哥老会,还是别的什么会党,基本都和“叛乱”纠缠不清。可以说,一部会党史同时就是一部叛乱(起义)史。这在《中国帮会史》(上编)《中国秘密社会通史》(卷三)等论著中可以清楚见到。这样的写作模式,看似以会党为主体,其实仍是以清方档案为依据。只用档案做研究,看到的自然只有叛乱。如著者所言,档案告诉我们的是事情的结果,要想理解事情究竟如何发生,需要找到更多的过程性材料并仔细解读。第三章“罗生门”,就通过这样的材料,展现出会党历史的 *** 过程。
材料之一是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抄本《先福奏折稿》,先福在嘉庆十四(1809)至十九年任江西巡抚。当时先福要处理边钱会萧烂脚案,在奏稿中,为符合法律条文,他修改了此案的罪状。乾隆三十九年法例曰:“其无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序齿结拜兄弟,聚众至四十人以上,为首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年少居首,并非依齿序列,即属匪党渠魁,首犯拟绞立决……”,即有歃血、盟誓、焚表等事,或不依年纪大小排列结拜顺序,刑罚会严重得多;聚集人数也是关键的因素。先福的奏稿修改了这些细节,比如萧烂脚“拜会”六次,原来有四次序齿(22人、40人、66人、40人),有两次不序齿(32人、39人),修改为四次不序齿(32人、39人、66人、40人)。这自然能将更多的人网进严重刑罚的范围。
先福奏折稿还涉及陈纪传案。关于此案,他早先上过一件奏折,主题是“民人争山酿命”,但不久后再奏,主题竟转变为“为结会匪徒占山酿命欲图纠众报复”,这个“微调”直接改变案件性质,将原来案情重点由原来的争端,转变为追查会匪。
著者注意到地方官在处理秘密结社时的两难,“处理得严苛,朝廷批评扰民;处理得轻忽,朝廷责备不当”,除此之外,还有更多我们难以知晓的考虑。这些材料,很生动地反映了地方官们微妙的心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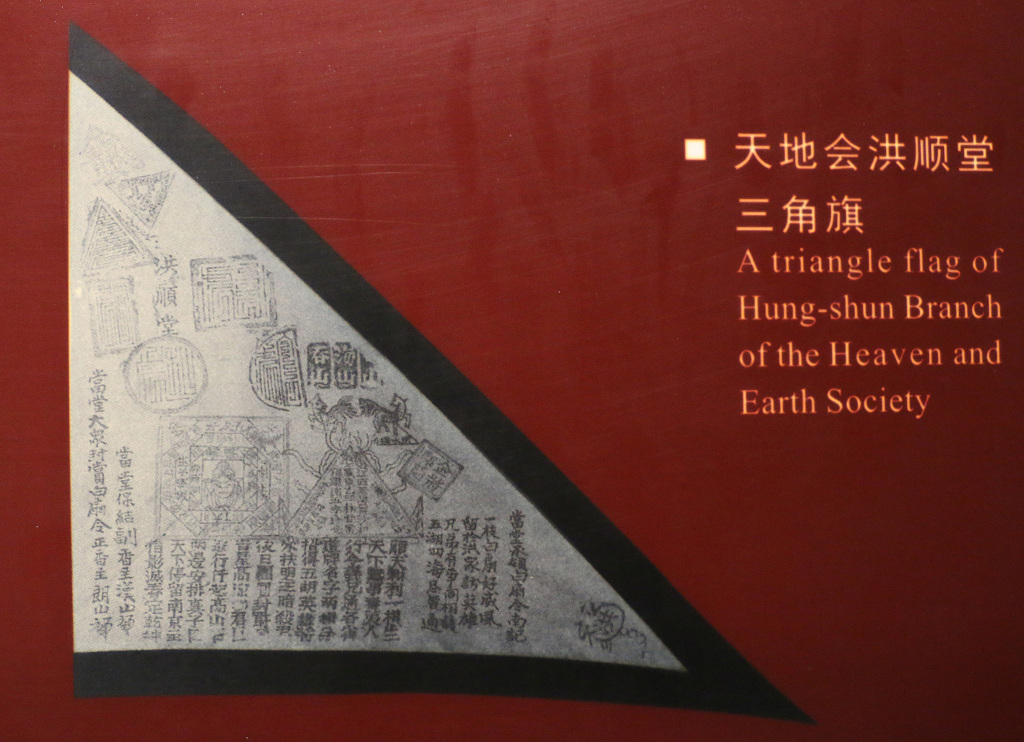
广州花都区洪秀全纪念馆,天地会洪顺堂三角旗。
材料之二是江西省泰和县县官徐迪惠的日记,全本影印收入《国家图书馆藏·中华历史人物别传记》。著者写作时用的是影印版,现已有整理版。徐迪惠,道光四年(1824)至十年任泰和县令。有一天,徐迪惠日记中记下食盐走私者闯卡的事情,事情本身并无异常,也和会匪无关。但不久后,有御史上奏称会匪与盐枭相勾结,影响地方治安,要求地方官剿捕。尽管两江总督与江西巡抚尝试否定御史言说,但无果,最后只能让步,将御史的附会变成了事实。如果没有徐迪惠的日记,单看御史们的奏折,也许只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因此,著者提示,“档案固然是很重要的历史材料,但是历史学者读档案,不可以不考虑档案书写过程的修改可以改变对于案件的报道”。(142页)
三、权威叙事模板的“反哺”
第四章“时势与场地”的故事从小刀会讲起。道光末年,福建发生了小刀会案件,组织者陈庆真出生于海峡殖民地(英国在马来半岛及周边群岛设置的殖民区),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二十二岁时回到厦门。时人,尤其是外国人,很相信小刀会就是天地会,但从起义的档案资料来看,小刀会与天地会的联系非常脆弱,那么,为什么时人那么相信两者有紧密的联系?著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明白,天地会在华侨社区的传播,与它在东南、华南的传播,并没有先后之分。”(156页)
东南亚华人社区有很强的自治传统,存在不少以籍贯等为根据的帮派,殖民者称这类机构为“公司”。著者发现,不少研究东南亚秘密会社的历史学者,都倾向于用晚出的文献,来说明此前地方华人帮派的天地会性质,他认为,“这倒令我们相信并没有当时的文献能证明天地会与19世纪20年代的帮派有什么关系” 。(161页)
英国殖民者最早介绍天地会的文章写于1821年,1825年天地会的名称开始频频出现于英国人的报告。大概从1840年代开始,随着华人移民的增长与党派斗争的激化,英国殖民地 *** 开始用“秘密与危险”来形容华人会党,同样的概念在中国人居住的香港也出现。
1845年,香港总督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发布了*三合会的汉文告示,这并不是因为香港发现了三合会,而是戴维斯以此与两广总督耆英达成交易:由他在香港追讨意图造反的三合会,而耆英对付盗劫了英国船的海盗。香港*三合会法律比海峡殖民地推行更早,之后被海峡殖民地模仿。
直到1854年,海峡殖民地才出现之一个会党与天地会有关的报告,报告是槟榔屿警察队长沃恩(J.D.Vaughan)所写,但故事内容模糊,只是之一次有人在海峡殖民地,用文字讲述当地华人会党以天地会故事作为它们的历史根源。
这些都说明,海峡殖民地华人帮派与天地会的实际关联,至此仍十分微弱;有的只是很多言说。
到1866年,荷兰人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将荷兰殖民地警察破案获得的天地会文献等材料,按照汉学传统全部翻译成英文,并考证部分内容出版。著者特别指出,“施列格书的重要性在于其变成了有关天地会资料的权威”,权威性的著作出版,“后果是所有扎根田野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学者都知道的噩梦——权威的著作可以影响地方上人士提供的资料”,“以后的研究者可以引经据典地替东南亚的华人会党加上天地会的外衣”。(176页)
同时,这个方向也非常符合殖民地官员的需求,1868年,调查槟榔屿暴动的委员会就特别引用施列格书来解析会党性质。更直接地说,“殖民地 *** 需要论证制度法例的合理性,天地会的传统正好赋予了会党反叛的性质,汉学家施列格的巨著更可以提供证明,不管事实上有没有根据。”(187页)
施列格书作为之一部完整的天地会著作,往往会被回溯天地会研究学术史的学者们重点提及。但以往从未有人从这一角度考虑其著作的影响,这正是著者“田野”眼光的表现。
四、哥老会:从通称到“实体”
与天地会一样,哥老会是另一个为人熟知的会党名称,频繁出现于19世纪后半期。
哥老会这个名词的出现,与湘军不可分割。在第五章,著者先梳理出湘军领袖曾国藩与这个名词的纠缠关系,其中关键节点是同治四年(1865)霆军闹饷事件,曾国藩日记一般不记批阅文卷内容,闹饷事件是个例外。起先,哥老会完全没有在闹饷的文件上出现,但下级军官试图以哥老会滋事为由减轻闹饷罪责,尽管愤怒,曾国藩最后接受这一看法,并上奏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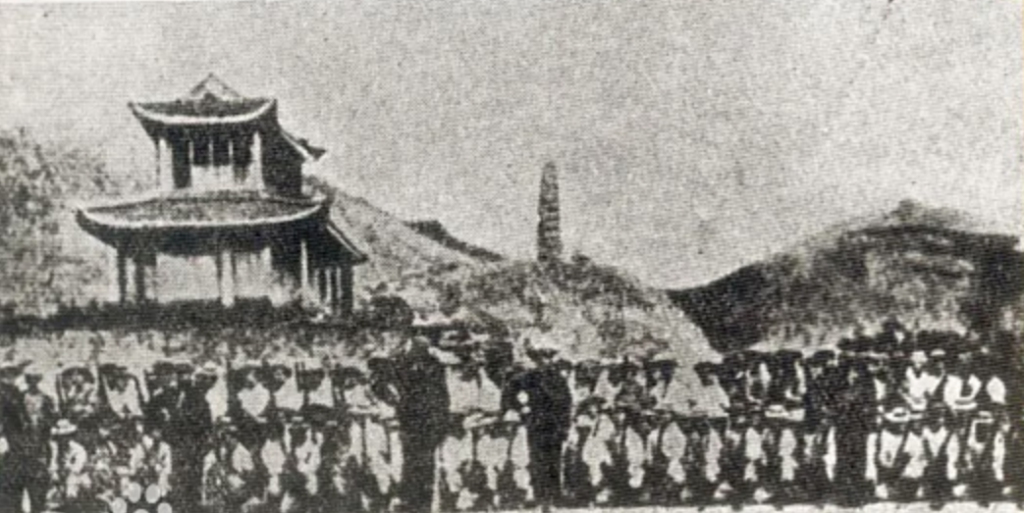
辛亥革命时期延安哥老会成立的武装
著者认为,曾国藩的奏折,以及报纸等文献的推波助澜,大大提高哥老会作为“通称名词”的知名度。“哥老会”已经成为标签,能够把边钱会等其他任何会都归纳于它的名下。
这是一个重要的论点,但是需要有更多“过程性”的材料具体论证。我这里刚好可以提供一则。约同治末年,湘潭县人龙化池被当作匪徒缉捕,同县士人罗汝怀有意拯救,写信给友人、乡居巨绅郭嵩焘,请其说项,称“近来之办哥匪不为不力,或直供不讳,或竟无供。直供者知不供无益,而徒受苦刑也;不供者实不知所以供也”。(《罗汝怀致郭嵩焘》(三)(三十三),孙海鹏、王瑜整理:《郭嵩焘亲友尺牍》,868-869、888页)无论有供无供,各类“匪徒”最后都会被归在“哥匪”这一通称名下。
光绪十七年(1891),梅森(Charles Melsh Mason)走私军火案,又某种程度上促成哥老会形象“实体化”。“实体化”,意思是哥老会并非实体组织,但已可以让很多人以为它是实体。梅森当年从香港走私武器到汉口,在上海被海关截获。受审时,梅森表示与会党有过接触,但没有供出同党,也没有说这些会党就是哥老会。
不过,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几个月后,却报告他找到了委派梅森押运军火的会党,为首者是已革提督李世忠之子李洪,他正在动员各省力量为父报仇。张之洞奏折成为哥老会“实体化”最重要的根据。
针对张之洞奏折内容,著者做出了如下的重要解读:“根据张之洞的调查,有没有李洪这个人实在不清楚,可以联系四省的会党为父报仇,也是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与其说哥老会在光绪中期已经建立了可以动员的跨长江四省的 *** ,不如说清 *** 通过顺藤摸瓜式的调查又把焦点调转,回到了地方上的保护团体。”(218-219页)
以往的研究,似乎都将张之洞奏折作为可以凭信的“史实”,并未太多考虑这些说法的可靠性。同样的,在光绪二十六年自立军起义中,张之洞又向朝廷报告了唐才常等自立军领袖勾结哥老会的情况,著者认为,“这些言辞又是一篇张之洞集供词之大成论证会党 *** 的大作”,当年的改革志士根本没有预料到戊戌政变,又如何在一两年之内动员长江流域的哥老会?(222-223页)也就是说,张之洞在哥老会“实体化”方面又一次做出杰出的贡献。
张之洞以供词 *** 会党 *** ,自然具有很高的难度;但如果考虑到李洪动员四省天地会起义为父报仇的难度,也许会觉得张之洞的活儿还是相对简单吧?当然,从论证的角度说,指出事件中建构的一面而未能说明本事,论证其实并未结束。这些问题本身非常复杂,值得更多讨论。
自立军的失败并没有减少革命党对哥老会的期望。光绪三十二年的萍浏醴起义,就是这种期望的展现。著者关于这一事件的解析同样精彩,比如说,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为什么习惯武力的会党首领愿意接受一些没有军事经验的年轻人的指挥?”(229页)而推敲萍浏醴起义过程,也可以看出涉及的会党并没有多少先设的从属关系。
在萍浏醴起义发生的时代,哥老会已被报纸公认为是革命党争取的民众支柱,不过,这样的支柱相当虚幻,一方面从未成形,另一方面又会随时瓦解。由此,著者总结说,“‘哥老会’只是地方上会党的通称。只有在革命传统之下,它们表达的反清情绪才可以达成一种统属。”(246页)这个结论也解释,何以清末依靠会党的诸种革命创举,从未取得过成功。
五、秘密社会没有秘密
说完上面的故事,让我们回到天地会。
如果以旧思路讨论天地会历史,起源问题就是最重要的问题。不过,参照哥老会的历史,会发现起源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像著者说的,“天地会是一个名词,不是一个实体的团体。在嘉道年间,有人利用天地会的名义组织拜会的仪式,拜会的仪式传播天地会实体存在的讯息”。(19页)而像张之洞一般的“认真调查”,只是“为天地会提供它存在的客观证据”。
由此,新问题便是,如果天地会并不是一个实在团体,为什么它会有这么大的跨地域影响力呢?其中关键,在于天地会的拜会仪式。
之一章“拜会”,从边钱会的故事开始。边钱会众将一文钱分为两半,当作结党凭证。作为结会符号,边钱比单纯的结拜有力,因为边钱这样的共通象征,能为组织提供形式上的统合。不过铜钱又有问题,它只是单一团体承认的符号,能够承载的想象太小。如前所述,天地会的故事仪式比边钱会丰富得多,这关系到拜会人群以外的大历史,关系到分散在各个省份的“五祖”后人。“当一群人举行天地会的仪式的时候,他们建立起的不仅是拜会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与他们想象之中的其他拜会群体建立了关系”。(38页)
同样的,对官府来说,天地会的跨地域组织 *** 也只是一种想象出来的错觉,官府在不同地方搜查到会簿之类的文献、捕捉到参与过类似活动的拜会者,“似乎又能为拜会背后跨越数省的人际 *** 提供证明。”(48页)天地会的扩散依靠着会簿的传抄,但这种扩散只是讯息扩散,而非组织扩散,只不过在拜会者和张之洞们的“循环论证”中,讯息扩散似乎真的变成了组织扩散。
不过,“扩散”还需要考虑另一个问题。随着讯息扩散,特别是天地会的名称列入《大清律》,天地会的秘密逐渐众所周知。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秘密会失去其效力,要保持秘密的有效性,“拜会一定需要变化,也越来越复杂,因为复杂的过程才可以确认秘密的独有性。”(56页)
第二章“秘密是怎样散播的”,梳理出天地会拜会仪式日趋复杂的过程,同时讨论怎样在拜会仪式上建立虚拟的天地会架构。著者认为,早期阶段(主要是乾隆年间),拜会仪式很简单,敬拜的神很可能就是天、地。到嘉庆年间,天地会仪式中设立祖师万提喜的牌位,用木斗插旗,以布搭桥,通过这些新设置,“原来让所有参与者成为同姓兄弟的仪式,开始演变为具有承传脉络的演绎场域”(80页),承传意味着尊卑、意味着等级,虚拟的组织架构逐渐出现。
秘密扩散之后,传会人需要维持住尊卑、等级,维持主导地位,因此需要构建出更多秘密的层次,仪式也要不断推出新的表演,后世流传的,细节更为繁复的所谓“黑话”由此不断出现。著者很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对话“不可能是主持拜会人与‘新丁’之间的互动,只可能是主持者相互配合的表演”。(92页)总之,在短短三四十年间,天地会仪式从神前结拜,演变为复杂而有戏剧效果的参拜。
著者多次援引社会学者齐美尔(Georg Simmel)关于秘密的理论,认为“正如血缘一样,与他人共同隐瞒的秘密也是一条社会关系的纽带。保密的特殊性,好像血缘,由一起保密的人所共有,其他人没有。所以,与血缘类似,秘密也可以缔造社会关系、社会团体”。(第6页)只是相较于血缘,秘密更加廉价。
不过,为了保存秘密,秘密需要承传。承传的后果是什么?著者将齐美尔的论述归纳成有趣的小诗:“传得多了,承传只是一种仪式。其实,除了怎样做仪式,我们都已经忘记了要保存什么秘密。他们/她们以为我们有什么秘密,最后发现我们的秘密就是我们没有秘密。”(第5页)
天地会的拜会就是这样,拜会给了参与者/非参与者一种我们/他们拥有秘密的感觉。实际上,天地会和哥老会的秘密就是没有秘密。这就是秘密社会的秘密。
该著作为“历史人类学小丛书”的一种,很好地展现出以田野眼光解读文献能够带来的巨大收获。历史学者“既要将文字材料放回到文字可能记录的限度之内,又要考虑文字记录以外可能发生的种种”。(267页)以往的学者,并非没有对相关思考惯性的反思。孙江在回顾天地会起源问题的争论时,就指出,“争论深化了人们关于天地会起源的认识,也暴露出了一个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即什么是‘真实性’的问题。两派观点虽然别异,但在历史认识论上却惊人的相似:都相信自己能够建构‘客观的’天地会历史。其实,无论是会书,还是档案,都不是客观的历史,仅仅是对历史‘客观’的叙述而已”。(《重审近代中国的结社》,42页)该著出版,不仅仅是重新阐述会党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关键在于引入更锐利的认识 *** ,并做出很好的研究示范。
本书篇幅不大,且著者写得十分生动,是近年来最有“活人感”的学术论著之一。这也是让我忍不住写下这篇小文的直接原因。不过,由于书中细腻的史料分析之处极多,承载的信息量超出一般,因此仍不算特别好读,也极难概括。以上的概括,只是勉力而为,或有未能符合著者原意之处,恳请著者、读者谅解。
最后想说,在该著论述中,跨地域、跨省份、具有庞大 *** 的“秘密社会”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也许真是这样,这样的“秘密社会”只存在于奏折、文集中,存在于研究者的想象中,而不是在活生生的历史情境中。以后的会党史研究,也许需要在该著基础上,在更具体的时空情境中,重新出发。
(本文承杨之水老师,任东峰、范丁旋同学批阅,谨致谢忱。一切文责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