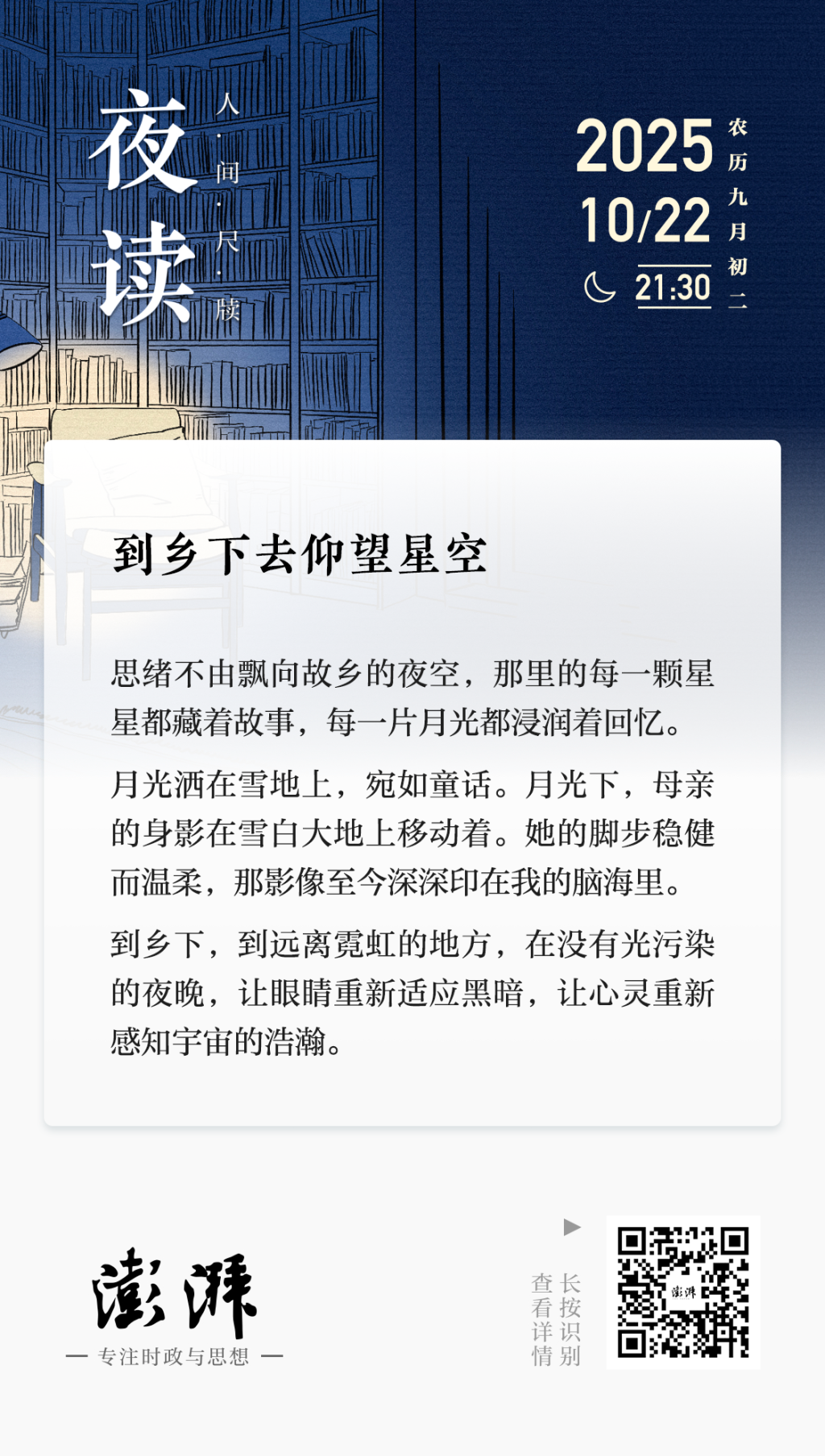华灯初上,我穿过车水马龙的街道,踏入东明湖公园。夜色中的公园宛如一块墨玉,静谧无声。我习惯性抬头,欲寻记忆中的明月与繁星,却只看见被城市灯火染成灰蒙蒙的天幕,宛如被蒙上了一层薄纱,将星辰的光辉尽数遮蔽。
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向故乡的夜空,那里的每一颗星星都藏着故事,每一片月光都浸润着回忆。

作者供图
“蛙声十里出山泉”,故乡的春天总是被蛙鸣唤醒。起初,是一两声若有若无的浅吟,似是在试探春天的温度;而后,三四声呼应着响起,由远及近,渐渐连成一片激昂的乐章,奏响在水田、沟渠、池塘之间。没有月光的夜晚,我和伙伴们便成了探险家,扎一个熊熊燃烧的火把,背一个竹编的鱼篓,深一脚浅一脚地踩进田中。调皮的鱼鳅、黄鳝仿佛嗅到了春天的气息,纷纷从泥洞中钻出来,在水中欢快地游动。
我们高举火把,橙红色的光芒在水面上跳跃,鱼鳅、黄鳝们像是被施了定身咒,呆呆地停在原地,眼中满是惊奇。我握着铁钳,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对准,轻轻插下去,“啪”的一声,夹住鱼鳅就往鱼篓里放。那长长的、滑溜溜的黄鳝可就没那么容易对付了,我好不容易夹住了它的下半截,正满心欢喜,它却突然用力一扭,“嗖”的一下,又溜回了水中,溅起一片水花。大多数时候,我们总要等到火把快燃尽,鱼篓沉甸甸的,才意犹未尽地往回赶。回家的路上,星星在头顶闪烁,像是为我们点亮的明灯,伙伴们还会扯着嗓子唱起不成调的小曲,歌声在夜空中回荡。
夏日的夜晚,是江南农家最闲适的时光。那时的小山村里,没有电风扇的嗡鸣,没有电视机的光影,更没有智能手机的蓝光。然而,夜晚从不寂寞。晚饭总是摆在家门口的坪地上,坪地边几棵高大的树木如撑开的巨伞,洒下一地阴凉。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自家种的蔬菜,饭菜的香气混着花香,令人陶醉。饭后,大人们摇着麦秆扇,坐在竹椅上谈天说地,分享着家长里短。孩童们则在周围嬉笑打闹,玩捉迷藏的游戏。月光爬上树梢时,和谐的左右邻舍便会自发地坐成一圈,听村上懂文化的大爷讲故事。
大爷摇着蒲扇,声情并茂地讲述着牛郎织女的传说,我们仿佛看到了牛郎在人间辛勤劳作,织女在天上织布,他们被银河隔开,只能在鹊桥相会。尤其是在农历月中,月光如水,倾洒在村庄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常常要闲聊到月亮偏西,哈欠连连,才依依不舍地收拾凳子,关门睡个安稳觉。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也是忙碌的季节。一天傍晚,生产队长吹响了哨子,通知大家:“吃过晚饭,大家统一去砍玉米秆!”我们借着星星的微光,一块田一块田地快速推进。玉米秆在手中“咔嚓咔嚓”地倒下,汗水湿透了衣衫。临了,生产队长发话了:“大家再坚持一下,有糯米饭犒劳大家!”真没想到,队长还留了一手。大伙一听,浑身又充满了力量,三下五除二就完成了任务。随后,顶着满天星光,迈着轻快的步伐,前往仓库后面的一户人家,去享受一顿香喷喷的糯米饭夜宵。
冬天的夜晚,大多是在家中烤火、闲聊或打牌中度过。然而,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年腊月十六七,下了一场大雪,母亲牵着我的小手,在雪夜里快乐地行走。那天,母亲和我到舅舅家喝喜酒,等到散场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舅舅家离我家不远,路上还有月亮挂在高空中。
月光洒在雪地上,银装素裹的世界宛如童话。月亮走,我也走,小小的我玩起了雪球,一路小跑在前头,时不时回头望向母亲。明亮的月光下,母亲长长的身影在雪白的大地上移动着。她的脚步稳健而温柔,那影像至今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而头顶的月光,在雪后的夜空中格外明亮,像是撒在天幕上的钻石,闪烁着清冷迷人的光芒。
如今,站在城市的夜空下,我不禁感叹:霓虹灯织成的光网,将星光稀释成微弱的叹息。那些曾在故乡清晰可见的北斗七星,此刻隐匿在人造光源的迷雾中,仿佛成了遥不可及的传说。
或许,我们该重新学会仰望。到乡下,到远离霓虹的地方,在没有光污染的夜晚,让眼睛重新适应黑暗,让心灵重新感知宇宙的浩瀚。愿有朝一日,城市的夜空也能重现繁星点点,让更多人领略到星空的壮美与神秘,让这份美好代代相传。